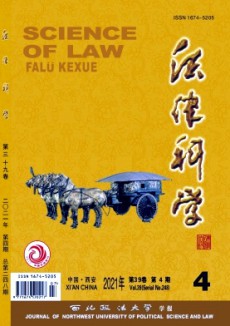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大全11篇
时间:2023-06-13 16:07:28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法律规范与法律规则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中图分类号: H111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6-0029-07
高诱,东汉涿郡(今河北涿县)人,著名训诂大家。现存三书注《吕氏春秋》、《淮南子》、《战国策》多集中于词义训释,但也不乏语词读音注释。这类音注据我们统计共有386条①,其中反映异读的音注虽然不多,但有限的材料本身仍说明了上古时期存在形态音变现象。沈建民提到,随着汉语形态音变的逐渐消失,很多异读材料难以揭示早期的形态语法规律〔1〕。于是有许多学者对把异读看成形态音变表示质疑,认为异读只是一种词汇现象或语义现象,也有学者把它看作音变构词的手段。我们赞成沈先生的观点,认为从语音变化的角度看,大多数异读仍应看作形态音变的反映。本文将从高诱音注异读现象入手,对语词的形态音变规律试作探讨。
一、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一些形态现象 1.异读区分动词致使和非致使
王力认为一般非致使动词读浊音,致使动词读清音〔2〕。周法高认为辅音清浊交替具有区分上古汉语自动词、使动词语法意义变化的功能〔3〕。包拟古认识到上古汉语可能有*s前缀,此前缀有致使意义的痕迹〔4〕。潘悟云、梅祖麟同意辅音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动词非致使和致使的构成形式,梅氏同时提出*s语素是一个致使化前缀〔5~6〕。舒志武提出致使化是*s前缀的重要构形功能之一〔7〕。梅祖麟举8例说明上古汉语*s语素的致使义〔8〕。郑张尚芳认为上古汉语*s是表使动式的词头〔9〕。潘悟云举11例论证*s的前缀致使义〔10〕。Pulleyblank提出前缀*在上古汉语中为非致使动词前缀〔11〕,其后Baxter、龚煌城、沙加尔等学者纷纷吸收这一观点,对前缀*展开讨论〔12~14〕。金理新在评定前人例证的同时,补充了大量例子对*s前缀的致使功能、*前缀的非致使功能做了充分说明〔15〕。高诱音注异读材料区分动词致使和非致使关系正是通过前缀*s、*交替实现的,其中前缀*s表示致使义,前缀*表示非致使义。
包拟古列举了以母和书母交替构成的同族词〔4〕,大体就是非致使、致使动词的关系。举例子五对,即施/施、豫/舒、夷/矢、绎/释、逸/失。潘悟云采纳了其中的“施/施”作为非致使、致使动词配对的例子〔10〕。
《淮南子·俶真训》:“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高注:施,读难易之易也。
施:《广韵》式支切,施设,亦姓。/施智切,易曰:云行雨施。/以豉切。
刘 芹 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语法形态规律探赜据高诱音注,施当读中古“以豉切”,上古音为*dar②,表示非致使义“延也”;而施在中古读“式支切”,上古音为*sthar时,则表致使义“使延”,可见两音有语法区别。根据文义,显然“施”为自动词;根据语法结构,“施”后不带宾语带补语,无致使对象。所以“施”为非致使动词,高诱为“施”所注读音与其语义、语法皆合。“施”字的这种语法形态音变在先秦文献中不乏其例,如《庄子·人间世》:“哀乐不易施乎前。”“集释:施,读为移。”〔16〕“施”表示“延也”义,为非致使动词。又如《国风·周南·兔罝》:“肃肃兔罝,施于中林。”〔17〕施,式支切,上古音*sthar,表示“使延”义,为致使动词。
2.异读区分动词自主和非自主
金鹏指出,藏语自主、非自主动词与语法结构有重大关系〔18〕。马庆株参考藏语动词的自主和非自主划分法,得出了现代汉语动词也分自主和非自主的结论〔19〕。金理新认为上古汉语更像藏语,除词汇手段(笔者注:即不同的词交替)外,还有相当多的动词是通过语音屈折表现自主和非自主差别的〔15〕,语音表现的手段有辅音清浊交替及*s、*后缀转换。高诱音注异读反映的动词自主、非自主变化是通过后缀*s、*交替完成的。其中,后缀*s表示非自主义,后缀*表示自主义。例如:
a.《淮南子·俶真训》:“古之真人,立于天地之本,中至优游,抱德炀和,而万物杂累焉。”高注:炀,炙也。炀,读供养之养。
b.《淮南子·精神训》:“是故无所甚疏,而无所甚亲,抱德炀和,以顺于天。”高注:炀,炙也。读供养之养。
养:《广韵》余两切,育也。/余亮切,供养。
《群经音辨》:“上育下曰养,余两切,书政在养民;下奉上曰养,余亮切。”
供养,指对长者或尊者必须做的动作行为,是说话者主观无法控制的,中古音余亮切,上古音*jaηs,表示非自主义。转化为自主动词后,中古读余两切,上古音*jaη,表示“养育”之养,动作行为是说话者主观可以控制的,即说话者可以选择养或不养的行为。高诱音注旨在说明其时的常用字“养”已有两读,有语法形态变化。“养育”之养的动作说话者可以主观控制,表示自主语法意义。为了反映“养”字的语法形态变化,作音时特别注明“供养”之养。
“养”之两读语法区别,文献多见。《尚书·大禹谟》:“政在养民。”〔17〕上养下,动作主观可控,为自主动词。读如常用音,即上古音*jaη。《左传·文公十八年》:“如孝子之养父母也。”《释文》:“之养,餘亮反。”〔17〕“养父母”为下养上,动作主观非可控,为非自主动词,上古音*jaηs。
3.异读区分动词及物和不及物
19世纪末,德国康拉迪认为中国语动词有及物和不及物的形态分别,由声母清浊交替实现③。此后,Maspero〔20〕、Schuessler〔21〕、Pulleyblank〔11〕等都认为及物、不及物动词清浊交替是上古汉语显著的形态现象。Pulleyblank同时指出不及物动词的浊辅音声母来自及物动词附加*前缀,这个*前缀导致词根辅音声母浊化,后来演变成浊辅音声母。这一观点后为Baxter〔12〕吸收。周祖谟〔22〕、周法高〔3〕、王力〔23〕、黄坤尧〔24〕对上古汉语不及物、及物动词语词形式之别都有认识。综上,上古汉语实现及物、不及物动词之间转换的方式除了声母清浊交替外就是附加词缀或词缀替换。高诱音注异读对动词及物、不及物语法意义的转换是由后缀交替实现的,表现为后缀*s表示动词及物性,后缀*表示动词不及物性。例:
《淮南子·说林训》:“渔者走渊,木者走山。”高注:走,读奏记之奏。
走:《广韵》子茍切,趋也。/则候切,《释名》曰疾趋曰走。
走,据高诱音注,中古读则候切,上古音*tjos,表示及物动词。高注的目的是为了跟中古子茍切、上古音*tjo的“走”区别,他明确指出“走山”的“走”是及物动词。“走”之不及物动词用例见《孟子·梁惠王上》:“弃甲曳兵而走。”〔17〕“走”为不及物动词,中古读子茍切,上古音*tjo。“走”之两读语法意义有区别,语音形态亦随之不同。
a.《吕氏春秋·季夏纪·季夏》:“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高注:渔师,掌鱼官也。渔读若“相语”之语。
b.《吕氏春秋·季冬纪·季冬》:“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高注:渔读如《论语》之语。
c.《淮南子·原道训》:“钓于河滨,朞年,而渔者争处湍濑,以曲隈深潭相予。”高注:渔,读告语。
d.《淮南子·时则训》:“乃命渔人,伐蛟取鼍,登龟取鼋。”高注:渔人,掌渔官。渔,读若“相语”之语也。
e.《淮南子·时则训》:“命渔师始渔。”高注:渔,读《论语》之语。
f.《淮南子·说林训》:“渔者走渊,木者走山。”高注:渔,读《论语》之语。
语:《广韵》鱼巨切,《说文》论也。/牛倨切,说也,告也。
高诱为“渔”注音时明确指出为“‘相语’之语、告语、《论语》之语”等,旨在说明“语”字两读,当区别开来。文中几例注音同为去声,“语”上古音*dηas,表示及物动词;转化为不及物动词后,中古读鱼巨切,上古音*dηa。高诱时代的“语”字有语法形态音变,故高注时对此常用字以“相语”、“告语”、“《论语》之语”等限定“语”字读音。
“语”之语法音变,文献习见。如《论语·乡党》:“食不语,寝不言”〔17〕,“语”为不及物动词,上古音*dηa。《论语·阳货》:“居,吾语女。”《释文》:“吾语:鱼据反。”〔17〕“语”后带宾语“女”,为及物动词,上古音*dηa。
《淮南子·时则训》:“陶气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高注:齐,读齐和之齐也。
齐:《广韵》徂奚切,整也,中也,庄也,好也,疾也,等也。/在诣切,火齐似云母重沓而开,色黄赤,似金出日南,又齐和。
齐,据高注中古当读在诣切,上古音*djirs,表示及物义;转化为不及物动词后,中古读音为徂奚切,上古音*djir。两音语法意义有别,“齐”系一常用词,高诱为其注音,其时“齐”字具语法形态音变。
4.异读区分动词施与指向
梅祖麟把有施与指向特性的动词称作内向动词和外向动词,并用“买、卖”这样的例子作了说明〔25〕。周法高将这一类型的词义转变叫“主动被动关系之转变”。金理新首次提出“动词施与指向”这一语法概念,认为后缀*s有动词施与指向的功能,并用大量例证作了有力论述,其中就有“遗、告”〔15〕。高诱音注异读表现动词施与指向变化的手段是附加后缀*s。例:
《淮南子·览冥训》:“猨狖颠蹶而失木枝。”高注:狖,读中山人相遗物之遗。
遗:《广韵》以追切,失也,亡也,赠也,加也。/以醉切,赠也。
高注特别指明“中山人相遗物”,意在说明“遗”不只一读。注文中“遗”当读中古以醉切,上古音*gjurs,表示动作有一个施与指向。上古汉语词汇系统中意义为“施与”的语词,在语音形式的选择上有一个共同点,即声调同是中古汉语的去声,此点金理新有详细论述。对于一个动词需要突出其动作施与指向时,就会附加一个表示施与指向的动词后缀*s。如赠,中古音昨亘切,上古音*tjes,《说文》:“赠,玩好相送也”;赐,中古音斯义切,上古音*stigs,《说文》:“赐,与也”;贷,他代切,上古音*thegs,《说文》:“贷,施也”等。
《淮南子·泛论训》:“乾鹄知来而不知往。”高注:鹄,读告退之告。
告:《广韵》古到切,报也。/古沃切,告上曰告,发下曰诰。
“告退”之告意在点明告字不只一读。注中“告退”之告当读中古古沃切,上古音*kug,表示“报告”义,动作由下对上,卑者对尊者完成;中古音古报切,上古音*kugs则表示上对下,尊者对卑者的动作,动作突出施与指向,语音形式上附加有后缀*s。
5.异读区分动词完成体与未完成体
沃尔芬登认为动转化s后缀来自于藏语动词完成体后缀s〔26〕,这一观点为许多学者接受,如白保罗、马提索夫等。梅祖麟通过对藏语名词后缀s来源的分析,似乎认为上古汉语名词*s后缀跟动词完成体有关〔25〕。潘悟云肯定了*s后缀是上古汉语的一个既事式后缀〔10〕。黄坤尧认为上古汉语动词有完成和未完成的区别〔24〕。吴安其专文讨论了上古汉语完成体〔27〕。诸家用于讨论上古汉语完成体后缀*s的例证并不丰富。金理新认为上古汉语动词有现时式和既事式之分,他举了上古汉语大量*s后缀动词表完成体的例子,同时给出了上古汉语未完成体后缀*形式的诸多例证〔15〕。所举例中有转引周法高采自《群经音辨》的例字“过”,新增例字“解”、“易”、“重”。高诱音注异读材料表现上古汉语动词完成式、现在式语法意义变化是由后缀交替实现的,即后缀*s表示动词完成式,后缀*表示动词现时式。例见下:
《淮南子·览冥训》:“故不招指,不咄叱,过归鴈于碣石。”高注:过读责过之过。
过:《广韵》古禾切,经也。/古卧切,误也,越也,责也,度也。
过,高注“读‘责过’之过”,中古读古卧切,上古音*kors,表示动词完成式,义为“过越”;而中古音古禾切,上古音*kor一读表示动词现时式,义为“经过”,两音语法意义分别清楚。此处高注表明其有明显的语法概念区别。
经典中对“过”字两义分别清楚,《释文》为其作注87次,其中见纽去声17次,见纽平声49次,兼注21次。兼注原因在于各家对两词意义辨別不清,因为随着上古汉语形态的消失,六朝人想要清楚分别两音之间的差别确实不容易。但两音这百分之七十多的井然分界,确实又说明它们之间存在区别。这一区别正是动词既时式、动词完成式之间的分别。具体例证详刘芹《经典释文“过”字音义辨析》一文〔28〕,此不赘论。
a.《淮南子·原道训》:“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高注:解,达也。解,读解故之解也。
b.《淮南子·修务训》:“以身解于阳盱之河。”高注:解,读解除之解。
解:《广韵》佳买切,讲也,说也,脱也,散也。/胡买切,晓也。/古隘切,除也。/胡懈切,曲解。
解,高注“读‘解故’之解”对应中古音佳买切,上古音*kli,表示动词的现时式(即现在时);“读‘解除’之解”对应中古音古隘切,上古音*klis,表示动词的完成式。两读音异义别,前者表示一种动作行为,后者则表示这种动作行为完成后的一种结果或状态,语法意义不同,其形态也相应发生变化。
文献中“解”字以异读区别动词现时式、完成式的例子比比皆是。《礼记·曲礼上》:“解屦不敢当阶。”〔17〕“解”为动词现时式,表示动作现时的状态“正在解除”义。《庄子·人间世》:“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释文》:“解,徐古卖反,又佳买反,注同,向古懈反。”〔16〕根据文义,“解”作“已解除”义解,陆氏以徐古卖反为首音,亦取此义为先。“解”表示“已解除”义,强调动作完成,表示动词完成式,语音与动词现时式之“解”自当分别。
a.《吕氏春秋·士容论·辩土》:“农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高注:易,治也。易读如“易纲”之易也。
b.《淮南子·俶真训》:“莫窥形于生铁,而窥于明镜者,以覩其易也。”高注:易,读河间易县之易。
c.《淮南子·俶真训》:“嗜欲连于物,聪明诱于外,而性命失其得。施及周室之衰。”高注:施,读难易之易也。
易:《广韵》以豉切,难易也,简易也,又礼云:易墓非古也。易谓芟除草木。/羊益切,变易,又始也,改也,夺也,转也。
易,高注“读如‘易纲’之易”及“读‘河间易县’之易”。还有一例出现在“施”的注音字中,即“施,读‘难易’之易也”。“河间易县”系一专名,此专名音读为中古音羊益切,上古音*dig,被注音字“易”文义为“变易”,为动词未完成体。“易纲”之易及“难易”之易中古当音以豉切,上古音*digs,表示动词的一种完成体形式,与其由之转变而来的未完成体形式即既事式的“易”相区别。高诱“易”字二音分别井然,语法概念清晰。
“易”之两读语法区别,文献多见。《庄子·骈拇》:“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16〕此易为“变易”之易,中古入声,上古音*dig。物变则易为而不变则难为,“易”通过附加后缀*s派生出“难易”之“易”。《庄子·人间世》:“有而为之,其易邪。”《释文》:“易,以豉反,后皆同。向、崔云:‘轻易也。’”〔16〕表示形容词“容易”义,中古去声,上古音*digs。
《吕氏春秋·开春论·审为》:“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高注:重读“复重”之重。
重:《广韵》直容切,复也,迭也。/直陇切,多也,厚也,善也,慎也。/直用切,更为也。
重,据高诱音注中古当音直用切,上古音*rdoηs,表示动词的完成式,其由之转变而来的动词既事式中古读直容切,上古音*rdoη。“重”之两义分别,语音亦自分别。“重”去声,副词。此副词系为动词动作完成后呈现的一种状态,故由动词转化而来的副词归为动词完成体一类。《庄子·让王》:“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释文》:重,直用反〔16〕。《吕氏春秋》文与此文相类,“重伤”之重高注“复重”之重,音与《释文》同,语法意义表示动词的完成体。
6.异读表示词性转化
古人没有名词、动词及虚词这些语法术语,但在他们的语感中对词性的辨认还是相当明确的。《经典释文·序录》云:“夫质有精麤,谓之好、恶(并如字);心有爱憎,称为好、恶(上呼报反,下乌路反)。当体即云名誉(音预),论情则曰毁誉(音余)……如、而靡异,邪(不定之词)、也(助句之词)弗殊。莫辩复(扶又反,重也)、复(音服,反也),宁论过(古禾反,经过)、过(古卧反,超过)。”〔29〕《经典释文》用对这类字的异读说明古人有语法词性区分。
周祖谟把因词性不同而变调者分为七类〔22〕。王力认为凡名词和形容词转化为动词,则动词念去声;凡动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23〕。总之,转化出来的一般都变为去声。黄坤尧将陆德明《释文》异读分为五项,其中有区别词性的异读〔24〕。金理新在“声母清浊交替”一章涉及语词异读跟词性之间的关系,详细讨论了辅音清浊交替跟名词、动词之间词性转换的关系。他在“后缀s”一章中论述了上古汉语后缀s(中古去声来源)具有名谓化、动转化、动词完成体及其它语法功能;在其它前缀、后缀章节多次涉及名谓化功能,即名词实现向动词转化的语音形态变化〔15〕。沈建民提到《经典释文》异读反映的形态时,其中一条即词性转化〔1〕。
综合各家观点,去声异读具有转化词性的功能。对于去声来自上古汉语s韵尾各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而这正好说明*s后缀具有区别词性的功能。
《淮南子·本经训》:“有不行王道者,暴虐万民,争地侵壤,乱政犯禁,召之不至,令之不行……”高注:言不行上令者。行,读行马之行。
行:《广韵》户庚切,行步也。/下孟切,景迹。
行,据高诱音注中古当读户庚切,上古音*gla,表示动词;转化为名词后,上古音*glas,中古读下孟切。
《淮南子·时则训》:“天子乃傩,以御秋气。”高注:傩,读躁难之难。
难:《广韵》那干切,艰也,不易称也。/奴案切,患也。
难:出现于高注“傩,读‘躁难’之难”。“躁难”之难当读中古奴案切,上古音*naans,表示名词;其由动词转化而来,中古音那干切,上古音*naan(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高注说明高音中“难”字有两读,具有区别词性的语法意义,故出注时特别指明“躁难”之难。
《淮南子·俶真训》:“至伏羲氏,其昧昧芒芒然,吟得怀和,被施颇烈,而知乃始昧昧晽晽……”高注:被,读光被四表之被也。
被:《广韵》皮彼切,寝衣也。/平义切,被,服也,覆也。书曰光被四表。
被,据高诱音注中古当读平义切,上古音*bals,表示动词;转化为名词后,中古读皮彼切,上古音*bal(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高注旨在说明文中为动词“被”,表义“服也,覆也”。
正如王力所言,“凡动词或形容词转化为名词,则名词念去声”。金理新将上古汉语名词变动词的实现手段概括为辅音清浊交替、附加前缀、附加*s后缀,同时并存辅音清浊交替或附加前缀。
《淮南子·泛论训》:“当此之时,一馈而十起,一沐而三捉髪,以劳天下之民……”高注:劳,读劳勑之劳。
劳:《广韵》鲁刀切,倦也,勤也,病也。/郎到切,劳慰。
劳,据高诱音注当读中古郎到切,上古音*raaws,表示动词;而中古鲁刀切,上古音*raaw(据潘悟云上古音体系),表示名词,两者词性的区别是通过附加*s后缀来实现的。高注指明文中“劳”义当为动词义,表示“劳慰”,并通过音注反映了“劳”字的语法意义,可见高诱音注中无时不渗透着强烈的语法概念意识。
渔,中古韵书注音只有一读,而高诱不厌其烦为其注音6次,且用有异读之语词“语”为其注音,指明它在文中读音当为去声,而《广韵》仅收其平声一读。渔,《说文》解为“捕鱼也”,动词。探其源,本字当为“鱼”。据孙玉文研究,“渔”字是由“鱼”变调构词产生的,在汉代读为去声〔30〕。他从六朝经师音注推断至晚六朝后期“渔”已读成平声,至唐代“渔”只能读平声,注去声只是“合韵”。《广韵》不论捕鱼的“渔”写成什么,都遵从后代读法,注成平声。可见,高诱音注无疑保留了古读,其音注的目的当是为了区别语词的语法意义,辨别词性。
二、高诱音注异读与形态的关系 潘悟云指出以下几种语音交替现象反映了形态音变:(1)韵尾相同而主元音相近的韵母之间的交替,即清儒所说的旁转。(2)主元音相同而韵尾部位相同的韵母之间的交替,即清儒所说的对转。(3)同部位的塞音,包括清浊和送气不送气之间的交替。(4)流音之间的交替。(5)同部位鼻音之间的交替。(6)词根加前缀音或加后缀音。(7)词根声母和元音之间加中缀。(8)长短元音之间的交替。(9)小舌塞音和舌根塞音之间的交替。(10)带次要音节的词和不带次要音节的词之间的交替〔31〕。从对高诱不多的音注异读材料分析来看,有两点结论可以得到肯定:
1.上古汉语无疑是存在形态变化的
从高诱音注异读材料来看,我们可确定以下几种语音现象与形态有关:(1)前缀*s与前缀*之间的交替。(2)前缀*s与无s前缀之间的交替。(3)后缀*s与后缀*之间的交替。(4)后缀*s与无s韵尾之间的交替。(5)去声与其他三声之间的交替。
高诱音注异读主要涉及的构词词缀有前缀*s、前缀*、后缀*s、后缀*。通过前文分析,我们可将各类词缀的构词功能概括如下,即:
前缀*s是一个致使动词前缀,具有致使功能。与之相对的是前缀*,是一个非致使动词前缀,具有非致使功能。两前缀常常通过语音交替实现语词致使功能、非致使功能的语法意义转换。
后缀*s语法功能较多,有表示非自主动词、及物动词、动词完成式、施与指向功能及动转化与名谓化功能。其中动转化、名谓化功能并不冲突,对此金理新已有详细论证〔15〕,兹不赘述。后缀*与后缀*s相对,具有表示非自主动词、不及物动词、动词现时式功能。在这三类语法意义上,两后缀有交替关系。
2.异读与形态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
潘悟云认为,古代汉语随着形态的消失,异读大部分也消失了〔5〕。形态与异读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确实,高诱音注中的“渔”字在高诱时代当还有两读,可到了中古,从韵书中保存的资料看就没有异读了,这跟它区别语法意义的形态音变消失不无关系。可见,语音的日趋简化导致异读无法存在,上古汉语的形态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就随之消失。可以说,语词异读与语法形态两者之间存在着相生相灭的关系。
(感谢冯蒸教授、金理新教授的指导,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文中错漏部分概由作者自负。)
参考文献:
〔1〕沈建民.《经典释文》音切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07:193,197.
〔2〕王 力.古汉语非使动词和使动词的配对〔C〕∥王力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485.
〔3〕周法高.中国古代语法·构词编〔M〕.台北: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1962:80,77.
〔4〕包拟古.原始汉语与汉藏语〔M〕.潘悟云,冯 蒸,译.北京:中华书局,1995:33,33.
〔5〕潘悟云.谐声现象的重新解释〔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87,(4):59,59.
〔6〕梅祖麟.梅祖麟语言学论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63.
〔7〕舒志武.上古汉语s前缀功能探索〔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社科版),1988,(6):98-105.
〔8〕梅祖麟.上古汉语*s前缀的构词功能〔C〕∥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1989:23-51.
〔9〕郑张尚芳.上古汉语的s头〔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0,(4):10-19.
〔10〕潘悟云.上古汉语使动词的屈折形式〔J〕.温州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1,(2):48-57.
〔11〕Pulleyblank,Edwin.Some New Hypotheses Connerning Word Families in Old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J〕.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73,(1):111-125,111-125.
〔12〕William H.Baxter.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M〕 New York:Mouton de Gruyter Berlin,1992:218-220,218.
〔13〕龚煌城. 从汉藏语的比较看上古汉语的词头问题〔J〕.语言暨语言学,2000,1(2):51-62.
〔14〕沙加尔.上古汉语词根〔M〕.龚群虎,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83-88.
〔15〕金理新.上古汉语形态研究〔M〕.安徽:黄山书社,2006:288,371,360,321,17,293-320.
〔16〕郭庆藩.庄子集释〔C〕∥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1:156,156,323,146,980.
〔17〕阮 元.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0:288,135,1865,2666,2495,2525,1240.
〔18〕金 鹏.藏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3:34.
〔19〕马庆株.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马庆株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160-191.
〔20〕Maspero,H. Préfixes et dériveation en chinois archaque〔J〕.Mem. Soc. Ling.de Paris,1930,(23):313-327.
〔21〕Axel Schuessler. What Are Cognates and What Are Variants in Chinese Word Families?〔C〕∥何大安.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古今通塞:汉语的历史与发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03:225-245.
〔22〕周祖谟.问学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6:101,93.
〔23〕王 力.汉语滋生词的语法分析〔J〕.语言学论丛,1980,(6):6,3.
〔24〕黄坤尧.音义阐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23,16,23.
〔25〕梅祖麟.四声别义中的时间层次〔J〕.中国语文,1980,(6):427-433,427-433.
〔26〕Stuart N.Wolfenden.Outlines of TibetoBurman Linguistic Morphology〔M〕.London:Royal Asiatic Society,1929:58.
〔27〕吴安其.汉藏语的使动和完成体前缀的残存与同源的动词词根〔J〕.民族语文,1997,(6):21-32.
〔28〕刘 芹.《经典释文》“过”字音义辨析〔M〕.语文学刊,2009,(5B):165-167.
〔29〕陆德明.经典释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3:3.
篇(2)
冲突规则本身对于系争的效力来源是什么,其效力依据何在? 这成为法律选择适用中突显的一个内在实质性问题。如果从法律规范作为一种有别于其他规范的特性上讲,其具有效力实在性。对此,凯尔森认为,我们所说的效力,意思就是指规范( norm)的特殊存在。说一个规范有效力就是说我们假定它的存在,或者就是说,我们假定它对那些其行为由它所调整的人具有约束力。由此可见,法律规范存在是以其能够成为对当事人法律关系确定的效力依据为前提和基础的,如果一项法律规范在对具体案件当事人最终权利义务分配中不起实效作用,或者其效力根本就未被受其调整的当事人所意识到,那该种规范本身能够证明成为法律规范的可能性都是不存在的。对前例中冲突规则来讲,其是否具有法律规范的本质属性就存在了疑问。
二、问题的分析
要分析冲突规则是一种法的技术性规定而非法律规范需要首先把握什么是法的技术性规定以及其与法律规范的异同。可以发现,该文是从对法的技术规定的界定入手,对于什么是法的技术规定,此文并没有过多加以论证,其直接引用权威著述,所谓法的技术性规定( 也称法律技术) ,一般是指创制和适用法律规范时必须应用的专门技术知识和方法,如表达法律规范的方法、整理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方法、解释法律或进行法律推理的方法等。借用此概念并基于以下理由,本文认为,该文对冲突规则及法的技术规定的论证是值得商榷的,冲突规则并不属于法的技术规定。
( 一) 从冲突规则的本身来讲
为了证明冲突规则不属于法律规范,该文指出了两者在逻辑结构上的差别,以此作为区分两者并进而将冲突规则归属法的技术规定的理据。其将冲突规则的范围部分横向地与法律规范逻辑结构中的假定条件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包括的是一大类法律事实,而后者是单一的事实,因此两者在数量上和程度上存在差异。如此论证,也正好与其所提出的,与法律规范相较,法的技术规定中的范围往往规定的比较宽泛,这一论断契合。对于这一论证思路,本文认为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该文存在一个概念运用上的逻辑错误,其称冲突规则范围中包含的是某一大类法律事实,这里使用了法律事实作为冲突规范范围所包涵的内容,但问题是,按照法理,一定的事件和行为之所以是法律事实,是由法律规范规定的。其在不承认冲突规则属于法律规范的大前提下,在对冲突规则结构的描述中提及只有在法律规范中才应具有的概念,这似乎不合乎逻辑。其二、该文希望通过数量或程度的比较,在冲突规则与法律规范的逻辑结构上寻找其关键的差异,但问题是,这种比较是否可行,能否将两种事物彻底的划分到两类不同的情形下去。本质的区别是划分不同归属的根本,而这里的所谓一大类与单一甚或比较宽泛等都是抽象的标准,自身都难以界定,更勿论用于区分归属。进一步讲,即使是单一的法律事实,其也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情况,从数量上讲也是难以用以衡量比较的。另外,该文也试图通过调控对象角度,将冲突规则与法律规范加以区分。其指出,冲突规则的适用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其更像是为法官所设立的裁判准则,而非给一般市民的行为规范。以此为理由,该文希望表达冲突规则所具有的如法的技术规定般专门性。殊不知,法并不只是评价标准,它也将是有实效的力量正是在法官那里,法才道成肉身。这条古谚表明,法律规范的适用对于法官而言同样是具有专属性。因此在适用过程中,冲突规则对于法官的需要程度与一般法律规范无异,而且实际上也并没有什么所谓专门的冲突法法( 院)规存在,对于该文的此种概括,恰恰相反说明了冲突规则依附法官的特性,使得其成为一种法律规范的外化。
三、问题的解决
通过上述辨析与总结,似乎可以认为冲突规则还是应该属于法律规范的范畴,但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因为一方面,对冲突规则的各种归属问题尚存不同的认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需要进一步加以澄清,另一方面,如果将冲突规则作为一类法律规范,其具有的许多较一般法律规范特殊之处如何理解,是否会改变对法律规范的基本法理都是值得进行探究。
篇(3)
中图分类号:D915.4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7.01.0018
关于宪法权威的认识一般都认为包括三个层面上的权威:法律上的权威、道义上的权威和政治上的权威[1]。在法治国家的建设中,宪法权威是其他法律法规制定的根据,也是所有组织和个人的最高行为准则,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与宪法相抵触,不得凌驾于宪法之上。从传统的法理观念看来,宪法权威的形成是基于宪法自身的至上性和强制性的法律属性,法律规则的规范性基础来源于其强制性,然而宪法权威的形成不必然是基于法律的强制性或宪法自身赋予的至上性,公民内心对于宪法的认知和认同状态对于宪法权威的形成应当同样重要,并且是宪法权威形成的关键因素。
一、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默示的认同
在传统的法治理念和规范视野内,在法律规则居于主导地位的社会中,人们对于法律规范有着明确的认识,并确定应当遵守法律,法律规范作为构建社会秩序的根本依据和人们的行为准则,其正当性来源于法律的规范强制性,而由法律规则所构建的规范秩序则是立足于法律规范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和强制心理效果,在分析法学的视野中法律的权威来自于制裁或者强权,法律的本质是靠强制制裁执行的者的命令[2]。法律的强制性是其成为社会基本规范的原因,社会秩序的建立必须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社会的其他事务和制度的建构应当以法律规范为参考并在法律的轨道内有序运行,依法治国的法治理念是被确认为最为优化的社会治理方案,支撑法治社会秩序存在和发展的是法律的形式和规范,并以国家对法律的保障和法律规则的强制性为基础。
法律规范的存在使得社会秩序的形成更具稳定性,在现代政治国家中,由美国所确立的政体成为世界各国纷纷效仿的模式,宪法自此被认为是构建现代社会秩序最基本的法律,美国政治文明的发展也使得秩序成为理想的社会秩序蓝图。然而在秩序的图式中必然有着对基本法律即宪法的形式强化,形式上的宪法规范影响着社会秩序的形成,法治意义上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就是法律规范,作为社会规范的一种,法律规范因其得到国家的认可并以强制力保障其内容得以实现,而具备了成为维护和建立社会秩序的根本因素。在现代国家,由法律规范形成的法律体系的核心是宪法,因而社会秩序是建立在人们对于宪法的认知基础上的,基本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则是来源于人们对宪法的认可。麦考密克在其Institutions of Law一书中所例举的“排队”例子说明了规范性秩序的产生基础,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在于一种非正式的规范性实践,而这种非规范性实践进一步构成了正式的法律秩序的基础,麦考密克认为人们之所以自觉地排队,正是因为这些行动者具有了共同的信念,知道自己应当怎么做,并“相信”别人知道应该怎么做,于是一种依赖于共同信念的规范秩序得以形成[3]。
在麦考密克的制度法学理论看来,社会秩序的基础和规范性来源是基于社会成员之间不成文的T例,一种对规范相互期待的信念,以此共同信念的实践就形成了一种默示的规范。与传统的社会秩序形成理念不同的是,制度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秩序的基础不在于者的命令或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而是来自于社会成员对于规范相互期待的认同意识,支撑社会秩序得以存在的是一种默示的规范和对此的默示的认同[4]32,宪法作为法律规范的核心,其所欲形成的秩序的基础应当是公民对于宪法规范的一种默示的认同。
二、立足于默示认同基础上的宪法权威
一般认为宪法权威是指一国宪法在法律上和实践中都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5],还有人认为宪法权威是就国家和社会管理过程中宪法的地位和作用而言的,其内容包括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的根本行为准则等方面[6]。从此种观念看来,宪法权威应当通过其在实践中的切实运行予以体现,同时在具体的宪法实施中体现其最高的法律效力和地位,从而彰显其权威性。然而宪法权威之所以能获得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公民对于宪法规范的默示的认同,这种默示的共同观念构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得以成立的基础,此与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有些许类似,但不同于社会契约的理论假设前提的自然状态的描述和公民让渡权利组成政府实现个体的联合[7]。立足于默示认同基础上的宪法权威是一种观念即公民共同接受“政府有权进行管理,公民应该服从政府和政府制定的法律”的共同观念,公民与政府共同的认同意识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默示的惯例,建立在默示认同基础上的惯例取得了对宪法和政府管理的承认,由此宪法才获得了其构建社会秩序、在社会的实践运行中取得最高的地位和法律效力。
法律规范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的基础是公民的默认认同意识,基于此,宪法作为法律规范体系的核心,其所确立的秩序必然也是以公民对于宪法规范所具有的默示认同的心理,建立在默示的认同之上的惯例对宪法予以承认,宪法乃至整个法律体系都依赖于此种简单的认同观念:足够多的公民相信其他公民也会像自己一样认同宪法的观念。从这个方面来看,宪法权威应当是以公民对于宪法自觉形成的依附感,并将其作为自己行为的根本准则,由此也成为整个社会秩序正常运转的基础。
默示的认同是一种内化于心的信念,不同于一般意义上国家以强制力作为后盾而推行的法律规范,基于默示的认同而渐进式养成的惯例或规则在压迫式的服从方面的阻力是较小的,公民个体对于规则或是事物的认知与赞同的情况下,可以预见的是公民个体会自觉在规则的指引下进行行为,并不会逾越规则的限度,个体的自由意志是行为的前提,默示的认同将个体的自由意志统一在一个合理的范畴内,进而使得一个区域内的共同体有了较为合理的依靠和支撑。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法律规则,基于社会契约而形成的权力与义务规则对于一定区域内共同体的公民都是普遍适用的,而宪法的有效性适用则依赖于共同体内的公民对于该规范的认同,其权威性的基础应当是共同体内公民对其内化于心的默示的认同。
三、宪法权威得以形成的因素
制度法学理论认为,法律规范性的来源或是法律秩序得以确立的基础是不同于凯尔森的实证分析法学抽象假设――“规范性基础”,也不同于哈特的承认规则理论,而是一种社会成员相互之间的默示的认同,基于相互期待和如何行为的“规范”,默示的规范成为了法律秩序的最终来源[4]4749。宪法同样如此,立足于默示的认同的宪法权威是在公民对于其他公民默认同样会和自己一样行为的前提之下形成的,宪法权威的形成也意味着宪法所欲构建的法治社会的秩序的确立,然而以默示的认同为基础的宪法权威是不同于主流法学理论所设想的那样,而是通过把庞杂的法律规则内化来理解他人的行为,并在此之上构建法治秩序。因此宪法权威的形成必然是另外一种路径,宪法权威的形成应当是其内生因素的使然,包括时间上的累积和宪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实践性“遗忘”。
(一)时间的累积――内生因素
以规范为核心的法律理论看来,法治的形成和实现必须依靠民众对法律规范的了解和认知,并应当将法律作为一个整体而被信仰,国家的法律的核心地位是个体经过“理性的反思”而建立的,建立于法律之上的秩序因而具有个体理性建构的色彩[8]。宪法权威同样应当是以公民对宪法规范的认知和了解为前提,通过个体理性认知到规范秩序乃至法治秩序的形成,宪法权威在此过程中也自然得以形成。与此理性化的秩序假设不同的制度法学理论认为,秩序的形成包括宪法权威的形成以非理性为基础,但是同样要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公民对于规范的认可并进而转化为个人行动,遵守宪法规范所确立的秩序,但是这一认识是非理性的,是公民自觉的过程。
无论是主流法学理论还是制度法学理论,其都认为法治秩序的形成包括宪法权威的形成且都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无论是主流法律理论认为的从对规范的认知到做出相应的行为的过程,还是制度法学理论认为的从规范到默示认同的惯例的转变,法治秩序的形成都依赖于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法律和秩序的形成马克思也指出:“只要作为现状基础的关系的不断再生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取得了有规则和有秩序的形式,这种情况就会发生。”[9]所以法律的形成或是秩序的构建无疑都是一个长时间的社会交往的产物,时间是法律的内生变量之一,同时也是宪法权威的内生因素。
因此宪法权威的形成必然需要时间的积累,时间的内生因素决定着宪法权威和宪法所欲确立的法治秩序的稳定性,法律在社会中被使用的时间越长,其被知晓的可能性就越大,个体的认知也就成为可能,无论是从社会风俗到法律规范或是直接的习惯,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权威性都会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
(二)社会性的实践――外生因素
制度法学理论认为规则并不是始终以规则的形式在日常生活中被公民个体所意识到,规则会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被不断使用,在此过程中有些会逐渐转化为个体的习惯,而规则在被使用的过程中必然会与社会性的实践相结合,与宪法权威形成的实践内生因素不同的是,这一社会性的实践是宪法权威形成的外生因素,其通过将规则外化为个体的习惯并形成稳定的内心认同感。
法律必须处于社会生活之中才会展现其规范性的一面,并使其作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因素更为明显,相对于时间的内生变量,社会性的实践是与现实密切联系的,通过社会生活将宪法规则在社会中的生命力彰显,以实现法律规则本身存在的目的,法律规则融入公民生活之中,融入公民社会性的实践活动中,会使得社会个体对法律规则或法律制度更容易承认和接受,而离开了日常生活中公民的行为实践和态度的支撑,宪法权威将会是被架空和边缘化的概念而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4]7275。因此,作为宪法权威形成的外生因素,社会性的实践会使规则更加成为自然,成为公民的一种自觉的习惯,将宪法规则乃至法律规则嵌入公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在习惯之中形成对于宪法的认同,宪法权威也就自然得以形成。
四、超越规则之治――从规则到习惯
(一)规则之上的习惯
从法的起源观念看来,法律最初的状态为习惯,其次则是社会风俗和惯例,者下达的一般性命令即俗称为法律[10],从成文法到不成文法,以习惯为基础的规则演变为法律,通过法律规则实现规则之治成为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法律规则源自习惯,在法律取得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之后,遵守法律则是社会成员的基本义务,法律规则的权威性也因社会成员的认同而愈加巩固。
法律规则从习惯中衍生而来,此种习惯是社会成员个体或大多数习惯性的行为方式,并被固定化而成为特定群体共同认可的行为模式,这时的习惯是规则之前的习惯,而在规则之后的习惯则是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公民对于规则熟悉的基础上,在面对现实实践时无意识或下意识而作出反应的行为,这是公民对规则经过内化之后形成的一种默示的认同习惯。所以在制度法W理论看来,社会秩序乃至法治秩序的基础是非理性的,就是对规则内化之后的习惯,公民遵守法律不仅仅是因为了解法律规则,而是因为公民已经将法律规则内化为自身的习惯,出于个人的习惯性思维和意识而做出相应的行为。法律规则只是公民学会守法的工具,一旦公民学会了如何正常行为,就不会去思考是法律规则让他们如此行为,当他们遇到类似的情形时,他们就会进行无意识的处理,而不会再去考虑法律规则是如何规定的,规则在此时甚至被“遗忘”,最终依靠习惯形成了社会秩序,此时的习惯超越了法律规则,成为公民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
规则之上的习惯比规则之前的习惯更具有稳定性,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宪法秩序或法治秩序因而更加稳固,而宪法权威也自然形成并获得公民对于宪法的尊重。
(二)个人习惯与宪法权威
人们对并非出于设计的规则和惯例的遵守,亦即对传统规则和习俗的遵循,乃是自由社会得以有效运行所不可或缺的条件[11]。惯例或习惯的确立使得社会成员的相互交往更为自由,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命令的结果,在规则之上的习惯为社会个体所习得并成为公民无意识的思维方式,个人习惯的确立和增长对于宪法的合法性的确立和法治秩序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主流法学理论对于个体对规则理性认知的假设过于理想化,公民不可能认知全部的法律规则,也不会每时每刻都在思考法律规则。所以个人习惯的获得是公民对于宪法乃至法律规则体系的非理性认知过程,这一从规则到习惯的转变的前提就是公民已经认同了整个法律体系的合法性,由此法律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和对社会秩序的构建超越了“规则――行为――秩序”的简单模式,从规则到习惯的内化过程使得个人习惯成为公民行动的影响因素甚至是决定性因素,而规则又具有了习惯的特征,习惯化了的规则构建的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因为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公民对于习惯化了的宪法或其他法律规则,不加思索地按照规则去行为,毫无疑问,这样的宪法秩序是非常坚固的。
法律规则的存在是为了影响公民个体的行为并由此而形成法治秩序,而习惯则是对法律规则的补充,但是规则之上的习惯却不仅仅是规范社会秩序的补充,经过了从规则到习惯的转变,个人习惯成为了公民无意识的行为思维方式,规则已经内化为公民的思维意识之中,宪法的至上性和最高性已成为一种信念,基于默示的认同而形成的宪法权威使得公民更加遵守宪法,宪法秩序的形成也水到渠成。个体习惯“取代”规则的同时也赋予了规则更加强大的生命力,同时在公民无意识的思维并行为的过程中“规则”被遗忘,以个人习惯为特征的宪法秩序是稳定的法治秩序,而宪法权威也在此基础上更加稳固。
五、结语
宪法权威的形成与树立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必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核心就是依法治国,树立宪法权威。法治秩序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宪法秩序的形成过程,实现法律规则之治并不仅仅是依靠法律背后的国家者的命令抑或法律的强制性,同时也包括公民对于规则或宪法的一种默示的认同,基于公民内心对于宪法的信念形成的一种认同,由此使得宪法权威得以确立,默示的认同过程是一个从规则到习惯转变的过程,具有个人习惯性的规则才是“活法”,具有真正的生命力,实现法律规则本身存在的目的,在以个人习惯为特征的规则所构建的社会秩序中,法律规则之治亦自然形成,而宪法权威则愈加稳定。
[参考文献]
[1]龚祥瑞.论宪法的权威性 [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190.
[2]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115.
[3]Neil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An Essay in Legal Theory [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16.
[4]李锦辉.规范与认同:―制度法学理论研究 [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
[5]胡维翊.宪法修改与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M]∥S崇德.宪法与民主政治.北京: 中国检察出版社,1994:56.
[6]何华辉,李龙.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建设[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234.
[7]卢梭.社会契约论 [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56,72.
[8]霍布斯.利维坦[M].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53.
篇(4)
作者陈林林,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310008)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是法律方法领域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四十年来持续位居国际法律理论的研究前沿。德沃金和阿列克希为代表的法律原则理论,以基于“规则-原则”二元规范模型的整全性、融贯性和“权重公式”,展示了法律原则适用中“理性化考量”的方法和判准,但被批评为“难以信服”、“基本没什么价值”。①法律原则的反对者甚至认为,法律方法论只需两种类型的规范:正确的道德原则和实定化了的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所以在法律方法论中并无一席之地。②不过,倘若否定法律原则的规范地位,那么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法律推理是否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也就成为了一个问题。实际上,藉由对规则、尤其是原则之类别的进一步细分,能对法律原则的适用过程――尤其是规则和原则的关系――给出一个更清晰的结构性分析,并回应、澄清对原则理论的一些诘难和误解。
一、规则的两种属性:自主性和总括性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陈林林:法律原则的模式与应用
法律原则理论作为一个系统的规范理论,见诸于德沃金对法律实证主义的批评。通过描述原则在疑难案件中的裁判功能,并藉此确立原则的法律属性或法规范地位,德沃金意欲否定“法律是一个由承认规则保障的规则体系”这一实证主义的基本信条,并据此重新划定法律的边界。在对Riggs v. Palmer案和Henningsen v. Bloomfield Motors案的解读中,德沃金论证了一种与法律规则全然不同的法律原则。具体说来:其一,规则是以非此即彼的方式适用的。对于个案来说,构成事实要件一旦确认,规则就要么适用(规则生效),要么就不适用(规则无效)。由于原则并未清楚界定事实要件,因此对个案来说,并不存在一条确定的、排他适用的原则。一条原则只是支持这般判决的一个理由,同时却可能存在另一个更优越、更适切的原则,要求作出不同的判决;其二,原则在适用中含有一个规则所没有的特性,即“分量”或曰“重要性”。当不同原则之间发生冲突时,法官必须权衡每一条原则的分量并择优录用,但这不会导致落选的原则失效。规则的冲突直接涉及效力问题,不予适用的规则会事后失效,并被排除在既定法律之外。③德沃金随后指出,形式取向的承认规则无法识别出法律原则,因为法律原则并非源于立法者或法院的某个决定,而是一段时期内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形成的公正感,需要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入手才能得到识别。④法律实证主义的巨擘拉兹,试图否认规则和原则之间的“质的差别”,来化解德沃金的批判。拉兹指出,某些貌似法律原则的评价性标准,只不过是法律规则的缩略形式;法律规则在相互冲突之际,也存在分量上的比较。⑤所以,原则和规则的差别仅仅是程度上的,而非逻辑上的。拉兹进而以社会来源命题为分析工具,强调了法律原则的事实属性。他主张即便法律原则是一种道德评价,那么它也是一种事实存在的公共价值标准。因此,“法律”的内容及其存在与否,仍可以参照社会事实、依据承认规则予以决定,而无需诉诸于道德权衡。⑥
德沃金和拉兹的争论,表明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各自可能存在双重属性或二元类别。法律规则作为一种一般化的规范性指示,由事实假设和行为方式或后果两部分组成。制定法律规则的理由或依据,是道德原则平衡或价值判断;换言之,法律规则是对各种道德原则进行通盘考虑之后进行理性选择的产物。法律规则一旦形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遮蔽(opaque)了规则背后的道德理由,即规则的适用不需要法官再行关注设立规则的一系列原则。判断规则是否可得适用,只涉及理解表述规则的文字,确认争议事实是否存在,并对照这二者是否一致。⑦当一条规则依赖若干相关的一系列原则的平衡得以正当化后,规则随后就排除或取代了那些原则――即所谓的一阶理由或基础性原则――直接适用于规则自己所涵盖的那类事实情形。这就是规则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特征的来源。排他性理由最重要的功能,在于排除了理由的通盘考量这个实践原则,即规则不仅排除了其他理由的适用,而且自我界定为采取特定行动方案的一个理由。规则具有的二阶命令、排他性的特征,显现了规则在适用上的一个属性,即规则的“自主性”。
规则的“自主性”地位,来源于规则的另一个属性――“总括性”,即作为一种一般性规范的规则代表的是一些全局判断,是对各种一阶理由或一系列原则进行通盘权衡后所做的行动选择。规则的总括性特征,让法官“依规则裁判”时不仅能节约成本,还能减少偏见、避免自行权衡出现错误。但要注意到,可错、偏见与成本,是理性行动所固有的缺陷,作为总括性解决方案的法律规则,本质上仍是一种“次优”而非“最优”的解决方案。因为最优的行动方案至少建基于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拥有有关个人处境与行为后果的完整信息;二是发掘出适用于该处境的全部理由;三是对于该理由适用的推理过程是完美的。这些条件的结合,才使得“理性的行动”呈现出“在获得有关行为人所处实际境况全面、准确的信息的基础上,找到对行为人的行为最佳支持”这个基本含义。但这是太过理想化的看法,因而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⑧
德沃金和拉兹皆指出,规则最主要的逻辑特征是其“决定性”:当一个具体的事实情形符合规则的适用条件,那么规则就必须得到遵循。自主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是排除一阶理由意义上的原则权衡的,或者说,在适用中是怠于或否定对一系列原则的权衡进行持续评估,因此其始终是具有决定性的。对于总括性意义上的法律规则而言,只要法院不改变对道德原则之间的基础性平衡的认识,那么它同样是具有决定性的。不过,当法院对基础性的道德原则平衡的观点发生变化时,总括性规则就会不断地得到修正。显然,较之自主性规则,总括性规则的“决定性”更弱而“内容性”更强。与规则适用中的自主性特征和总括性特征相对应的,是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⑨
二、原则的两种模式:理性化和最佳化
对于个案裁判而言,自主性法律规则必然是有拘束力的。当法官遇到了既有规则未予明确规定的个案时,如果要贯彻一致性和平等对待,那么依据德沃金的理论,法官能采取的合理方法是根据一系列原则――这些原则能最佳地证成一系列相关的、有拘束力的自主性法律规则――来判决案件。如果所有这些法律规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那么法官可以认为,那些为规则提供正当性的法律原则在道德上是正确的。当然,法官也可能认为,某些自主性规则在道德上也可能是错误的。在此情形下,法官往往会主张,依据能从道德上正当化那些长期有效的自主性规则的次佳原则是合适的。次佳原则为道德上存疑的一些自主性规则做了最直接的辩护,藉此允许法官在判决新的案子时,能尽量与现行的那些规则保持一致。这种与规则自主性观念相辅相成的原则适用过程,因为仍然以一致性、可预测性等形式价值(次佳原则)为最优判决目标,被称为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⑩
前述分析表明法院(乙)认同先前判决设立的规则R,但支持理由却不同于法院(甲)。在这种情形中,法律原则的理性化模式和最佳化模式实际是重合的,因为最终的行动方案是相同的。但是,如果纯粹基于法律原则的最佳化模式的分析思路,那么法院(乙)应追求个案相关的一系列相关原则的最佳平衡,因此不一定受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的拘束,尽管法院在原则平衡时仍然要考量到可预测性、一致性等第二位阶的原则。换言之,法院(乙)在跨越适当的认知门槛后,可以法院(甲)的判决推理或结论,例如否定作为规则R之正当化基础的原则C2,修改规则R的事实构件,乃至否定规则R本身。当然,废弃规则R这样的重大法律变动,必须基于一些德沃金“整全法”意义上的整体性理由,即视为是错误的规则或判决,必然落在不能依最佳化证立予以正当化的那部分既定法律的范围之内。显然,基于最佳化模式的法律推理,还内置了罗尔斯式的审慎明智、协调一致的“反思性平衡”:在普遍性的所有层面上做出深思熟虑的判断,其范围从关于个人具体行为的判断,到关于特定制度和社会政策之正义和非正义的判断,最终达到更普遍的信念。这意味着一条原则的法律地位部分地依赖于一种规范性标准,这个标准要求原则的内容和分量居于道德合理性的适当范围之内。法官必须诉诸于自己的道德信念和识别力,来判断这个标准是否得到了满足。换言之,法官们必须和自己进行道德论辩,而不单单是审查和以往其他人的道德推理相关的社会事实。藉此也再一次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因此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难案件的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可以显现为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
作为一种司法裁判理论,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是有一定解释力和说服力的,但也难免于若干困惑。限于篇幅,此处只讨论隐含其中的三个基本问题:A、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C、原则适用的方法论。问题A所指的法律原则的“规范属性”问题,和反对法律原则的学者所提的问题相关却并不相同。亚历山大和克雷斯曾强调:法律原则既无法律规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定性优点,又不具备道德原则具有的道德正确性优点,因此在法律方法论中没有一席之地。前面的论述已指出,法律原则是独立于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但很显然,法律原则在行为指引方面的确是不同于法律规则。这种“不同”的表面差异是行为指引上的确定性程度,实质差异是某个法律体系中的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又是“裁判规范”,但法律原则仅仅是一种“裁判规范”。行为规范和裁判规范的划分,可追溯至边沁的理论。边沁曾以刑法为例指出,“规定犯罪的法律与对犯罪施加处罚的法律,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它们管辖的行为完全不同;适用的对象也完全不同”。一条“禁止杀人”的规则,既是社会公众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杀人案件发生后法官必须考量适用的裁判规范,并且对于公众和法官来讲,“禁止杀人”都是一条明确的法律规则。相反,一条“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利”的原则,尽管也是社会公众应当遵守的道德行为规范,但一般公众在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并无恰当的能力(例如法律素养或法感)和信息(例如检索以往判例)――因此也无义务――去识别该原则是否是规范某一具体事项的一条法律原则。不过依据法律原则理论,一旦这类争议被递交到法官面前,法官就有义务去识别并适用与个案相关的法律原则;此外,判断一条道德原则是否是法律原则,取决于法官是否认定其得到了制度历史的支持,而与社会公众的认识或判断无关。换言之,法律规则既是行为规范也是裁判规范,其适用对象既包括法官,也包括生活在某个法律体系中的社会公众;法律原则是一种裁判规范,它的适用对象仅仅是法官。
“法律原则的适用对象仅限于法官”这一命题无疑会招致批评,因为在适用法律原则进行判决的那类疑难案件中(例如泸州遗赠案、Riggs v. Palmer),当事人最终显然受到了法律原则的拘束。不过,这种批评只看到了裁判的表象。以泸州遗赠案的一审判决为例,纳溪法院实际依据《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这一原则,针对遗产继承规则的效力设定了一条“第三者继承例外”的新继承规则。法云“一般条款不决定具体案件”,正是将《民法通则》第7条具体化为个案规则后,法院才否定了遗嘱的效力和第三者的继承权。因此一个补充性的亚命题是,“当法律原则适用于待决案件时,必须先具体化为一条个案法律规则;这条新创设的法律规则必然是可普遍化的,它既适用于社会公众,也适用于法官”。用阿列克希的“原则间的竞争法则”(Law of Competing Principles)转述之:当法律原则P1在C的条件下优于法律原则P2,并且,如果P1在C的条件下具有法效果Q,那么一条新规则R生效,该规则以C为构成要件,以Q为法律效果:CQ。
藉此转换到了问题B:适用法律原则的司法语境。一个已有的共识是,依据“禁止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裁判纪律,唯有在“规则用尽”的疑难案件中,方得考虑适用法律原则。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和“裁判规范”的定位,都表明原则裁判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司法”,而是一种创设规则的准立法性法律实践。事实上,德沃金的法律原则理论,引证的就是以法官为中心的普通法司法实践。离开普通法司法的语境,法律原则理论中的若干关键词――例如“制度性支持”、“先前判例”、“分量”、“”――的内涵就会引发歧义。因此,在司法体制和法官角色存在重大差异的大陆法系,尽管成文法中存在不少概括性条款或原则性规定,但法院是否可以根据最佳化模式进行规则创制并进行裁判说理,始终夹杂着诸多需澄清的问题,诸如法院的地位和功能、法适用和法创制的区分、法不溯及既往等等。
第三个基本问题是原则适用的方法论。法律原则的“分量”、“最佳化”等属性,从字眼上就表明原则裁判的关键,是用法政策式的权衡或类推去获得判决,其间必然诉诸对相关的不同后果及其可取性所做的比较和评估,即利益衡量。就如麦考米克所言,倘若判决所依据的那些相互竞争的类比、规则或者原则存在于法律之内,并表明判决为既有法律所支持――尽管不像明晰的强行性规则所提供的支持那般明确,那么法官有权作出相关的评估并使之生效。德沃金后期实际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整全性意义上的、向前看的结果导向论者。原则理论的支持者阿列克希,则进一步精细化了结果考量式的衡量方法,建构了一个复杂的“权重公式”:W1-i,2-j=(I1×W1×R1+……+ Ii×Wi×Ri)/(I2×W2×R2+……+Ij×Wj×Rj)。不过,所有这些努力――包括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理论――回答了一些问题,却又制造了一些新问题。
四、结语
哈特认为在法律规则不能给予判决以完全指引的案件中,裁量权的运用是在一些标准和政策指引之下进行的。不过,哈特对这些标准和政策存而不论,并否认其是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恰恰是德沃金这样的法律原则论者所反对的。法律原则的两种模式为原则裁判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结构性分析,还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不是纯粹基于系谱的,也不可能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它是独立于法律规则和道德原则之外的另一类规范依据――“裁判规范”。“裁判规范”的定位,保证了在遇有规则漏洞的疑案裁判中,基于法律原则的判决推理仍然是一种区别于普遍实践推理的、“部分自治”的推理模式,尽管这种源于普通法司法的推理模式在方法论和制度环境上遗留了一些有待澄清的问题。
注释:
①See Brian Leiter, The End of Empire: Dorkin and Jurisprudence in the 21st Century, 36 Rutgers Law Journal, 2004, p.165.
②Larry Alexander & Ken Kress, ‘Against Legal Principle’, ed. in Law and Interpretation, by Andrei Marmo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326, 327.
③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24.
④Cf.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105-17.
⑤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9-30. 麦考密克认为,原则“实际是一种更概括的规范,是若干规则或若干套规则的合理化结晶”。See Neil MacCormick, Legal Reasoning and Leg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232.
⑥Joseph Raz, 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9, p.53.
⑦Alan H. Goldman, Practical Rules: When We Need Them and When We Do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7.
⑧T. M. Scanlon, 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32.
⑨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2.
⑩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5.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
Richard Posner, ‘Pragmatic Adjudication’, in The Revival of Pragmatism: New Essays on Social Thought, Law and Culture, Morris Dickstein ed. 1998. cited from Adrian Vermeule, 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87.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796,801.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40.
Joseph Raz, ‘Legal Principles and the Limits of Law’, 81 Yale Law Journal, 1972, p.823.
Ronald Dwork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343.
斯蒂芬・佩里的分析较为繁琐,下述行文对其进行了概括梳理,Cf. Stephen R. Perry, Two Models of Legal Principles, 82 Iowa Law Review, 1997, pp.801。
[美]约翰・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正义新论》,姚大志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Bentham, A Fragment on Government a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430 (W. Harrison ed. 1948). Cited from Meir Dan-Cohen, Decision Rules and Conduct Rules: On Acoustic Separation in Criminal Law, 97 Harvard Law Review,1984, p.626.
Cf. Robert Alexy, A Theory of Constitutional Rights, trans. by Julian Riv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54.
篇(5)
中图分类号:DF0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81(2011)05-0058-05
H.L.A.哈特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法哲学家之一,无论是与富勒的争论,还是“哈特-德沃金”之争,他始终处于当代西方法学思想交锋和论辩的另一端,引领并推动当代英美法理学的发展。因此,发掘和研究哈特的法律思想,既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评价哈特的理论贡献,又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代英美法理学发展与变迁的思想脉络。
哈特的重大理论贡献是,在一般法理论中引入了内在视角(a internal point of view)的因素。但很不幸的是,这一概念经常为人所误解或误读。考虑到内在视角在哈特理论中的重要地位,为澄明哈特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的关联,笔者将根据自己的研读和理解,综合分析哈特内在视角的两个问题,即内在视角的定位及其与哈特理论立场的关联问题,以反思哈特法律实证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理论意义。
一、内在视角的提出及其涵义
哈特提出的内在视角,被视为迈向理解法律及其实践之本质的关键步骤。与传统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如奥斯丁和凯尔森不同,哈特基于社会规则的观念发展出一种新的法律实证主义理论。一方面,哈特驳斥了奥斯丁的简约主义,即把法律简化为者命令的做法,并以“抢匪情境”@为例说明法律不等于单纯的者命令;另一方面,他还驳斥了凯尔森的规范性简约主义――后者采取了双重的简化步骤来理解法律规范:第一步把法律界定为“应当是什么”的客观实在;第二步则把底线层面的应然实在简化为最高层面的应然实在,并依次进行三种不同的简化,即法律权利首先简化为法律义务,法律义务继而简化为法律规范,法律规范又最终简化为应然实在。哈特认为,法律规范不应简化为法律义务规则,还存在着授权的法律规则,后者决定着法律义务规则的确认、修改和存废。
根据哈特的社会规则理论,仅在规则被实践的时候,社会规则才存在。社会规则的实践通常由两个方面的要素所构成:(1)社会成员在行为模式上的趋同和聚合,以至于形成一种普遍的、稳定的常规行为模式;(2)社会成员对此行为模式持有广泛共享的批判反思态度,它表现为所有社会成员应当去遵守共同的行为标准,并批评和谴责那些行为偏离者。因此,尽管社会规则与社会习惯在行为常规的意义上存在相似性,但社会规则具有下列明显的特征:首先,偏离于社会规则,将导致社会成员对其行为偏离的批评;其次,这些批评被认为是正当的。这一正当性意味着,依据社会规则来评判不同行为的做法不应受到非议和谴责;最后,仅当社会成员把既有的社会行为模式视为行为的共同标准,社会才具有或存在一个社会规则。易言之,当其成员对特定的行为常规采取一种内在视角时,社会才会存在一个相关的社会规则。
哈特认为,在一个具有行为规则的社会里,“关注规则有两种可能的方式:要么作为一位外在观察者,他本身并不接受这些规则;要么作为该社会的一位成员,接受这些规则并以之为行为指引”。根据这一区分,哈特告诉我们,以第二种方式关注规则的社会成员,总是采取一种内在视角来看待这些规则。内在视角意味着接受规则者以一种批判反思态度来看待这些规则。根据这一界定,“接受规则”和“批判反思态度”是内在视角概念的两个关键词。
首先。接受某一社会规则就是把规则所载明的行为模式视为群体成员应予遵从的共同标准。它要求把规则视为行动的理由和证成条件,作为主张、要求、批判或惩罚的基础,而且作为确立这些要求和批评之正当性的基础。“(接受)存在于个人的常规倾向中,他们把如此的行为模式既作为未来行为的指引,又作为批判的标准,它可能正当化各种要求和不同的压力形式。”。这等于说,采取内在视角的人不管行为动机如何,他意图接受规则的指引并遵从规则的行为模式;与此同时,他可以批评那些不守规则的人,并运用“错误”或“不当”等评价性语言来表达其批评。
其次,批判反思态度最好被理解为既包含一种认知维度,又涵括一种意志要素。它的认知维度涵蕴着一个行为模式――在具体情境中如何行动的一般化范式一的观念,它具体表现为一种对行为与情境关联性的抽象感知能力。简单地说,对一项社会规则的认知,主要体现为对相对抽象的规范内容的理解和把握,这一规范内容涉及在什么样的具体情境下应当为或不为特定行动的事项。由于行为和情境相关性的感知力通常要求人们理解当前行为或未来行动的意义,因此认知成分还包含着一种评价自身行为以及思考如何行动的能力。这与“知识即力量”是密不可分的。批判反思态度中的意志要素,则体现在拟想的行动情境中从事特定行为或不行为的某种意愿或偏好。对待规则的批判反思态度,意味着在接受规则的前提下按照规则内容从事特定行动的行动意愿或偏好。换言之,即便接受规则者行为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必定有遵守规则的行动意愿或动因,否则接受规则的成员要么不愿意遵守规则的行为模式,要么不接受规则所要求的行为模式为评价行为的共同标准。
二、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和哈特的理论立场
为更好地把握内在视角概念的意义,我们必须在一个内外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中确定内在视角的准确坐标,进而阐述它与哈特之理论立场的关联性。
(一)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
在考察哈特有关内在视角的观点之后,学者们发现,哈特在论述法律或规则的内、外在视角时前后并不一致。由于内在总是相对于外在而言的,那么哈特的前后不一致主要体现在对外在性的不同指称上。在哈特的意义上,“外在”有时指称的是物理的距离,有时指称的是用以分析行为的手段,以及又指称对待所涉规则或体系的态度。我们可以在哈特的著作中分别发现相应的线索,如,一方面,哈特曾说,一位外在观察者“虽然自身并不接受社会规则,但却可主张该社会成员接受这一规则,并因此可从外部提及该社会成员以内在视角来对待这些规则的方式”;另一方面,哈特又提及“一种极端的外在视角”,它指的是这样一类外在观察者,他“甚至不诉诸于内在视角之方式……而仅仅满意于记录可观察行为的常规性”;再者,哈特还似乎曾把不法者的视角归之为一种外在视角。为此,通过鉴别不同的外在性类型,有论者从中总结出四种内、外在视角的区分形式:(1)跨文化观察者的外在
性,他可以理解其他的行动者以内在视角来看待社会规则的性质;(2)自然科学家的外在性,他仅仅记录其他行动者的行为常规,而不太关注行为者的动机和态度;(3)不法者的外在性,他拒绝接受规则并仅在预测法律的不利后果时关注它们;(4)无法理解法律融贯性和体系性之参与者的外在性,他仅仅是非常熟练地仿效其他内在参与者的行动,却并不认同法律的体系性和融贯性。
外在视角的多样性似乎意味着,它可以分别对应不同类型的内在视角。因此,要准确厘定内在视角的坐标位置,必须先构建一个合理的、符合哈特使用意图的分类学体系。为此,我们或可借用美国学者司格特・夏皮罗所提出的实践和理论之区分,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关于内在视角的分类学体系。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实践,其实践参与者必然是与法律打交道的当事人或法律人。这类实践参与者对待法律的实践态度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种是内在化的态度,即把法律规范作为行动理由的接受态度,这是一种典型的好人视角,即大多数遵纪守法的良好公民所持有的实践态度。哈特认为,他们必须是社会的大多数,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良好的法律秩序。另一种态度则是美国大法官霍姆斯所提出的坏人视角,它是一种典型的投机心态,它设想着,人们之所以遵守或服从法律,仅仅是为了避免与之相伴随的制裁和惩罚,而不是因为规则要求如此行为。从一定程度上说,坏人也是一种法律实践的内在者,虽然他关注法律的目的仅仅是厌恶法律制裁。因此,无论是内在化态度还是内在者的坏人视角都是一种实践立场,它强调内在于法律实践的参与者如何理解法律实践的规范意义。由于内在视角是一种接受或认同规范的实践态度,因此不以接受规范为基础的坏人视角虽然是一种实践态度,但却可被限定为一种外在态度。
而从外在于法律实践的立场来理解法律实践的诸方面,隐含了一种理论视角的可能性。持有理论视角的人,并不反求诸己,而仅仅去描述和理解其他的法律参与者是如何依据法律规范而行事。这一点与彼得・温齐对哈特的影响有很大关联。对于温齐来说,理解一个社会不同于理解自然,后者依据因果律来解释自然现象;理解一个社会现象,必须涉及到行为动机和行为理由的范畴。温齐的理论立场,可被称为一种参与者视角的诠释或理论说明,即根据社会规则来说明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动机和理由。哈特所自赋的描述社会学径路正是这一理论视角的一个典型,它旨在描述社会成员如何看待并回应法律规则的要求。相对于内在参与者的内在视角而言,这种诠释的理论视角仍然是一种外在视角,尽管它必须关注并考察参与者的内在视角。除此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同的理论视角,它仅仅满足于记录和描述社会行为的内容和频度,而不关注行为者的行为动机和理由。哈特把这一行为主义的描述立场称为一种极端的外在视角。
综上,我们可以在下述分类学体系框架中发现内在视角的清晰定位:
从这一结构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内在视角作为实践视角的一个支类,它与霍姆斯意义上的坏人视角均以实践的内在者为基点。两者的区别在于,是否接受法律规范,并持有一种内在化的实践态度――正是这一态度决定着实践参与者(即内在者)的分化。为了强调内在视角的实践性和接受态度,哈特曾在不同的表述场合下,把与内在视角并列的其他三种视角理解为一种外在视角。换言之,如果单纯以内在视角的接受态度为尺度,那么,无论是霍姆斯的坏人视角,还是外在观察者和研究者的视角,都是一种相对于内在视角而言的外在视角。这种相对性体现为不同的外在视角分别展现出一种相对应的外在性。
(二)哈特的理论立场
陈景辉博士在《什么是“内在观点”?》中认为,哈特的内在观点是对接受观点的描述,因而“不是内在参与者的实践观点,而是研究者以内在法律实践的者的角度,对于法律的解释”。这一观点似是而非。之所以“似是”,因为他通过援引夏皮罗教授的论文,强调了内在视角对规则实践的接受态度;而最终又是错误的,因为哈特对内在视角的描述本身是一种外在视角,即一种理论维度的外在视角。陈景辉博士恰恰混淆了哈特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之间的区别与联系。
哈特运用内在视角的目的在于,指斥以制裁为中心的法律实证主义思想无法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然而,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如其在《法律的概念》一书前言中所宣称的,是一种“描述社会学”的立场。之所以是“描述的”,“因为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不以任何证立为目标;它并不寻求通过道德或其他的理由,去证立或推荐我在一般性说明中所描述的法律制度的形式和结构”。在描述的立场下,哈特不是置身法律实践的参与者,而是借由一般描述实践参与者的行动来理解法律的性质。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实践的内在视角。那么,该如何理解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与内在视角的关联呢?
最早给出一个恰当解释的是英国法学家麦考密克教授。他在哈特思想之评传中指出,哈特法学思想的方法论立场是一个介于内在视角和外在视角之问的“诠释”视角:一方面,它全面分享内在视角的认知成分,即理解人们为何如此行事的模式;另一方面,虽然它能够完全理解内在视角的意志力成分,却并不接受和分享这一成分的内容,即意愿根据上述行为模式而行动。其他学者相继接受这一看法,并分别给出了相同的论述和说明。例如,比克斯就认为,哈特的方法进路是诠释的,因为它试图通过一种实践参与者如何看待实践的方式来理解这一实践的内涵和意义;夏皮罗也认为,作为一位法理学家,哈特实际上是从一个外在的诠释视角来观察和描述法律的。
外在的诠释视角意味着,哈特把自己当成是一位中立的观察者。由于法律实践涉及不同行为者的行动理由和行为动机,要理解法律实践的社会意义以及法律本质,理论家就必须通过说明和解释内在实践者的行为模式和行动意图而予以揭示。从某个程度上说,作为外在观察者的学者,必须凭借对实践参与者的理解和效仿,以揭示法律的本质是什么。要言之,一个事关法律本质的法律理论,必须说明内在视角的功用。
说明法律的本质是什么,并非给出一个有关法律是什么的概念定义,而是通过对法律义务的说明,来展示义务的规则约束性。说一个人有某一项义务,等于说他落在某项规则的约束之下。落在一项社会规则之下,隐含着社会的大多数对该规则的内在接受和认可,这正是社会规则之实践理论的核心要点。法律规则的效力,来自于一个基础规则亦即承认规则的确认和鉴别。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法律规则与社会的其他规则,如道德、宗教规则得以界分,并保有一种根本不同的规范性质。
三、内在视角的理论意义
虽然哈特自身的理论立场不是一种内在视角,但是他提出内在视角的重要贡献在于,“一个关于法律本质的理论必须要安置好内在视角”。那么,内在视角究竟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这里,笔者想从两个方面来展开,一是内在视角在哈特法律思想中的理论意义,二是内在视角的方法论价值。
首先,对哈特来说。内在视角的提出是为了说明以制裁为中心的法律理论之不足和缺陷。这种缺陷体现在它忽略了内在视角的存在。一种法学理论要成为普遍的理论,即能够说明法律体系的存在以及法律思想和话语的可理解性,那么它就必须认可规则接受的实践态度,一种实践参与者的内在视角。先前的法律实证主义者以制裁为中心的理论范式,只能有效说明部分法律实践者的行为动机和模式,即以畏惧制裁、计算苦乐的心态来对待法律。而事实上一个文明有序的社会中,大多数人应是接受并服从规则的良好公民,他们对待法律的态度不只是为了预测并规避法律制裁的发生和降临。只有兼顾法律实践者的内在视角,即承认实践者对社会规则的接受态度,方能更全面地揭示法律实践的全貌。
其次,内在视角能够有效地说明社会规则的存在,因此哈特得以提出社会规则的实践理论。它认为,共同体内的社会规则,是由该社会的某种社会实践形式来所构成的。其主要任务在于解释次级规则(尤其是承认规则)的效力问题。在哈特那里,承认规则构成一国法律体系的效力标准,即“任何规则都要通过符合该承认规则所提供的判准,才能成为此法体系的一员”。问题是,承认规则作为法体系的终极规则,其效力的根基又源于何处呢?为此,哈特重新转换了提问方式,把承认规则的基础效力问题最终转化为一个社会学的事实问题。如果承认规则是存在的,那么追问其效力基础的问题就是多余的。承认规则的存在是一个典型的事实问题,其最终确立仰仗于社会成员是否形成人所共知的行为模式以及对此模式的规范性态度。
最后,它还有助于人们理解法律实践的性质,并发展出一种法律陈述的语义学。内在视角的提出,不是为了说明法律活动的道德性或合理性,而是为了说明它的可理解性。既然法律实践的参与者把法律构想为一套由权利和义务所组成的社会制度,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规定权利和义务的特定规则。换言之,如果我们不能明白和理解人类行为是否符合某一规则,那么我们也将无法恰当地理解,在规则存在之处,人们思考、话语和行动的整体风格,以及这一风格所型塑的社会规范结构。
以上是内在视角之于哈特理论的意义。但是,哈特的理论视角不是一个纯粹的内在视角,而是分享了相关认知要素的诠释视角,因此才会有把哈特的理论径路视为诠释转向的观点――它的主要目标是描述性的,即描述社会如何看待法律规范的性质。然而,批判的观点认为,要恰当理解和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缺少参与者的内在视角是不可能的。换言之,哈特使用诠释视角来说明法律的规范性,是很难站得住脚的。基于这一原因,有论者认为内在视角应被视为法理学的方法论基调,因为要充分说明法律的规范性,研究者必须从参与者的视角出发来描述和理解法律的意旨和功能。正是出于这一信念,不少论者均吸以内在视角作为自身理论的方法论基础,从而成功建构一些独具特色的法理论。
篇(6)
作者马驰,天津商业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天津300134)
自罗纳德・德沃金以法律原则为肇端向哈特式的法律实证主义发动攻击以来,由这一论题引发的讨论几乎构成了半个世纪以来法律理论或法理学研究领域最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围绕着法律原则,已有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类,相互联系却又具备各自的独立性。第一类研究主要涉及法律的概念,即区别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是否存在,如果存在则对回答“法律是什么”这一法律概念问题产生何种影响,尤其是,现有的法律实证主义能不能在坚持自己基本立场的情况下,回应与法律原则密切关联的各种责难。第二类研究是有关法律原则的方法论,这类研究基本上已经肯认了法律原则的存在,重点在于,区别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之后,无论它们的区别是何种意义上的,原则究竟在个案判决中充当了何种作用,对于法官来说,它的适用有哪些特殊的要求和特征。不难发现,无论上述哪类研究,在逻辑上必然要以“法律原则是什么”这一本体论问题的妥当回答为前提。法律原则的本体论问题是本文讨论的基本范围。我将以法律原则已经存在为前提,检讨其存在的条件是什么,即其效力标准(criterion of validity)是什么。我力图证明,原则与规则无论在适用方法论上存在多大的差异,也不能简单地说,相对于法律规则系谱的或形式的效力规则,法律原则的效力准则就是基于内容的;此种二元划分简化甚至遮蔽了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复杂性,造成了规则与原则之间某些不必要的对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法律规则与法律原则在本体论上的差异不应该被夸大。
一、效力标准的含义
在法律理论的研究中,如同很多名词术语一样,效力一词含义并不总是十分清楚。在我看来,人们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使用法律效力这一术语,并以此产生了多种相互区别却又相互联系的效力标准的含义:
其一,效力是法律的约束力(binding force)。汉斯・凯尔森曾提到,效力是法律规范针对其所调整的对象所具有的约束力,一个有约束力的法律也就是一个有效力的规范。①我国现行的某些法理学教科书也采取了此种用法②,“法的效力是对其所指向的人们的强制力或约束力,是法不可缺少的要素。”在此意义上,效力标准实际上是法律之所以有约束力的标准或原因。法律效力的此种定义实际上与法律的规范性或权威性如出一辙;尤其是,由于法律的约束力必定是针对人们行动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在实践中表现为人们的行动理由,故当引入行动理由这一重要概念之后,对法律约束力问题的研究已经被有关法律权威性讨论所取代。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没有必要再使用效力一词来与法律的权威性相以混淆。
其二,在语义学的意义上理解效力④,将效力视为法律规范为真的标志,进而将效力标准视为法律规范的真值(truth value)条件。法律规范要以命题的方式加以表达,作为命题,它或许可真可假,这样一来,一个真的法律命题就是有效的法律,相反则是无效的。命题的真假通常受制于某种条件,这种条件便是其真值条件。例如,“火星上存在生命”这一命题的真值条件是,仅当火星上存在生命,该命题为真。然而,对于一个法律命题来说,称其为真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问题在于,我们或许可以借助所谓真理符合论来判断一个事实命题的真假,但法律命题作为规范命题或价值命题的真值条件却似乎难有定论,甚至无所谓真假。例如,逻辑实证主义者就主张,价值命题无法证实,没有真假可言,当然也就没有真值条件。⑤实际上,命题的真值概念是用来处理命题演算的工具⑥,将之引入法律理论有关效力标准的讨论,对问题的化解并无直接的助益,反而徒增了不必要的争议。
其三,效力是法律规范存在的标志,因此效力标准就是法律规范的存在条件或前提。在这个意义上,法律的效力是法律的存在方式,因为没有效力,法律就不存在了,无效的法律等于没有法律⑦;当我们确定某个法律是有效力的时候,我们的意思首先是的确存在这样一种法律。如果法律效力是法律存在的标志,那么效力标准的含义则在于,由于我们不总是任意地判断某一规范是不是法律规范,而是会使用一个或多个标准来对相关规范进行鉴别,这里的标准决定了相关规范是否是法律,这便是法律的效力标准。H.L.A哈特创造性地使用了承认规则(the rule of recognition)这一术语来指称法律的效力标准,在一个社会中,总会存在这样的标准,来决定什么样的规范能够算在这个社会的法律,即便这一标准的内容在不同社会中会有所差异,不同学者对这一标准性质的认定也有所差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承认规则实际上是法律规范的存在条件或前提。这便是本文所采纳的效力与效力标准的概念。当然,这里提到了承认规则,并不暗示效力标准规则一定是单一的一般性规则。实际上,本文的目标恰是要表明,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具有复杂性。浙江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马驰: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基于系谱抑或内容?
效力标准的这一含义需要与认知标准加以区分。在将承认规则视为效力标准的情况下,承认规则可能被当作法律的认知(epistemic)⑧标准或手段,是获得法律规范这一思维过程的工具。至少在《法律的概念》正文中⑨,哈特将承认规则视为一个单一的一般性规则,例如英国的承认规则是,女王议会制定的就是英国的法律。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一个对英国法律一无所知的人或英国法律的初学者想要知道英国的法律究竟是什么,那么“女王议会制定的就是英国的法律”的确是他们认识英国法律的快捷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规则当然具有认识功能。然而即便如此,也必须区分作为效力标准的承认规则与作为认知标准的承认规则。实际上,法律的效力标准是判断法律本身的合法性(legality)准则,是法律存在的前提与条件,它所具有的认知功能是偶然的。对此,朱尔斯・科尔曼曾举过一个极为有趣的例证⑩:想象这样一个简单的法律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法律的效力规则是,“凡德沃金说的即是法律。”这无疑是该社会的承认规则,但对于识别或认知法律来说,最可靠的规则却是,“听拉兹的”,他知道这个社会的法律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效力标准与认知标准是可分离的。不仅如此,当法官进行个案裁判时,判断何为法律,与法律如何适用至个案事实,也可能是两个并不相同的活动。在我看来,区分认知标准和效力标准意义重大,很多有关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争议其实是对法律原则认知标准的争议,申言之,是将法律原则如何有效这一问题,与如何认知法律原则这一问题加以混淆。也即是将法律原则在适用方法上的争议,看作法律原则效力标准的本体论争议。对此,下文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二、德沃金论法律原则及其效力标准
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界定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主导着人们对法律原则的认识。在里格斯诉帕尔默案中,德沃金认定法官最终使用了“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而不是法律规则,得出了正确的判决结果。在德沃金看来,法律并不仅仅由规则构成,它还包括原则。而原则与规则之间,存在“逻辑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规则是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来适用的,如果规则规定了既定的事实,那么当案件出现此种事实时,它就必须被适用;而在没有这种事实出现的情况下,规则对判决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原则具有分量(weight)和重要性的维度,而规则不具有这一维度。在特定案件中,可能适用的法律原则或许存在多个,对于哪个原则应该被使用也常常是有争议的,法官需要对各个原则就个案而言进行其分量的平衡或衡量,才可能得出其正确的判决。原则和规则是否具有分量和重要性维度的这一区别还引发了它们之间的第三种差异,即在一个法律体系中,当两项法律规则相互冲突时,除非存在调整这种冲突的规则,否则其中一条必定无效――法律的规则体系不能容忍规则之间的冲突。但若冲突发生在两项原则之间,则不会导致原则的无效,无非是,法官此时只需断定相互冲突的原则中的哪一项要更为重要一些。
德沃金之所以要在法律体系中区分出不同于法律规则的法律原则,是为了攻击以哈特理论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其要义在于,哈特的法律实证主义使得法律难以容留法律原则的存在,而法律原则的存在又是难以否认的,因此哈特的理论必须被抛弃。德沃金认为,按照哈特的看法,法律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们由某个权威机构颁布,例如由立法机构制定,或是由法官创制的;就此而论,作为法律规则的效力标准,承认规则是一个系谱(pedigree)的检验标准,它只能按照规则的形式或来源来确定或识别法律。如果承认规则是一个系谱规则,那么法律原则就无法通过这种规则进入到法律中。原因是,法律原则并不来源于立法机构或法院的特定决议,而在于法律专业领域与公众当中长时间所形成的妥当感(sense of appropriateness),只有在此种妥当感的支持之下,法律原则才可能作为法律而持续下去。在此种论证之下,德沃金试图将法律原则的效力与道德论证或原则的内容联系起来――法律原则之所以能够作为法律而存在,不是因为它的谱系或来源,而是因为它的内容是公平正义的,符合某种道德层面的要求或标准。
借助此种论证,德沃金显然向我们提供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这一标准首先不同于法律规则的效力标准,法律规则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的系谱或来源,即它是由权威机构颁布的。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却不在于此,法官在认定诸如“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是法律时,并不会去考虑这一原则系谱或来源,他并不关心究竟是谁或制定了这一原则,他的问题在于,这一原则在特定的案件中是否公平正义,是否能够被某个道德准则所容纳,是否被法律专业人士和公众的妥当感所支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法官就可以认定该原则属于法律。因此,可以在这个意义上主张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的,或者说是基于道德论证的。
仔细考察德沃金法律原则的概念,不难认定,德沃金工作的重心在于司法裁判活动,他主要借助法律原则在适用的意义上与法律规则存在较大的差异,来推断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存在“逻辑上的差异。”然而,如果仅仅依据德沃金的上述论证就得出结论说,判断一个原则是否属于法律原则,确定其内容是否符合特定的道德标准是唯一的方法,以至于主张法律原则唯一的效力标准就是基于内容的非系谱标准,并以此区别于法律规则系谱的效力标准,则是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简单化和一般化了。实际上,法律原则效力标准需要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
三、基于系谱的法律原则
或许是因为竭力将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效力标准归结为系谱规则,以便展开攻击,德沃金似乎没有注意到,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有时也可以是系谱的。即是说,我们可以因为某个原则的系谱或来源,断定其可以作为法律原则而存在。而这种基于系谱的法律原则当然依旧可以满足德沃金的原则概念。对此,至少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立法机构或其他权威机构的法律文件中确立了某个原则,该原则因为这种确立而具有法律效力。或者因为出现在有约束力的判例中,因而具有法律效力。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第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的伴侣,在家庭中地位平等。”夫妻平等原则当属于德沃金意义上的原则而非规则,然而,中国传统社会男尊女卑的伦理观已经盛行了千年之久,除非能够证明,这种观念在1950年前后突然被社会成员集体放弃,代之以男女平等的观念,否则就难以主张说,该原则是因为法律专业领域和民众中长时间形成的“妥当感”,或是经由道德论证,才成为法律原则的。不仅如此,在成文法系国家,由于人们通常将立法是否有规定视为法律效力的条件或标准,便出现了这种情况:同一法律原则可能既出现在权威立法中,又获得了某种道德论证的支持,此时,主张该法律原则是仅仅基于内容而不是因为权威立法的规定这一观点可能难以得到捍卫。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规定了公序良俗原则,几乎所有对这一原则的引证或研究都会提到《民法通则》这一权威法律文件原文;至少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中,很难想象,在缺乏该权威法律文件支持情况下,人们能够主张公序良俗是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可见其效力标准在于该原则的谱系或来源。
其二,法律原则的效力因社会民众或法律专业人士的共识而获得,但这种共识与道德伦理无关。德沃金主张法律原则的效力必须因为社会民众和法律专业人士的长期形成的妥当感才能被确认并存续,他认为此种共识一定与道德论证存在必然的关系,亦即共识形成的原因在于法律原则内容的道德性,并由此得出结论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的。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当然可以基于道德的理由形成共识,并因此产生妥当感。但同样有可能的是,这种共识有时与道德判断没有关联。其实,正是考虑到这种与道德无关的共识,哈特提出了基于惯习(convention)的承认规则理论,认定法律的效力可以与法律内容的道德性无关,而只需依靠法官群体的共识。那么,如果法官或社会民众对某一原则存有此种共识,该共识是否可以作为该原则成为法律原则而存在的充分条件呢?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可能的。例如,在诉讼程序中,法官的活动必定要受到法律约束,英美法中的法官在法庭上常常沉默不语,只是居中主持双方律师的法庭辩论或交叉询问;而在大陆法系中,法官要活跃得多,会通过言语等各种方式引导当事人和律师,控制法庭。如果法官在法庭上的活动不符合各自的原则,则被认为是怪异或不妥当的,然而,这种制约法官活动的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在于特定社会中法律群体的共识或惯习,对此并无明显的道德依据,也无需经过道德论证;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何人们通常不在这一问题上主张英美法系的法官要比大陆法系的法官更为高明或拙劣。
四、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
前文已经说明,某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与规则类似,都是基于系谱或来源的;这并不会否认的确有些法律原则难以按照系谱或来源来决定其效力。对于这类法律原则,德沃金和柔性实证主义的共识是,它们是因为其道德性才构成法律原则的。但这种道德性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此,我们仍然做更为细致的区分。
首先需要马上澄清的是,道德性至多是此类法律原则效力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是因为,如果所有道德上正确的原则都是法律,那么所有的道德原则同时也是法律原则,这种将道德与法律完全划等号的看法自然是谬见。对此,德沃金认识到,如同法律规则一样,法律原则必定要获得某种制度上的支持,法律原则所获得的制度支持越多,它的分量就越重。然而德沃金马上指出,这种制度支持不应也无法等同于哈特所说的承认规则,原因依然在于,原则的确定需要原则在一系列变化和发展中的相互交错的标准,这些标准难以被归纳为一条简单而绝对的单一指示或承认规则。无论德沃金对承认规则的上述限制是否成立,都不会影响到这一结论:在单纯的道德正确性之外,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包含了法律制度本身提供的标准。在许多疑难案件中,由于事实与规范不对称,案件所涉的法律原则看起来好像只是因为其道德性并借由法官的法律推理而出现的,其中并不涉及制度支持。以帕尔默案为例,从表面上看,适用“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而剥夺帕尔默的继承权好像更加符合某种道德观,于是该原则便是一条法律原则。但这至多表明,由于该案在事实上的特殊性,该原则因此具有道德性,却不能说明该原则仅仅因为此种道德性就能够成为法律规则。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官所做的判决就完全是个道德裁定,他根本无需用法律原则这一说法掩盖自己的道德推理。在这个意义上,法官在帕尔默中的法律推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抉择,而是对已经存在法律原则进行适用和取舍的过程。
当然,在德沃金对法律原则的认识框架中,毕竟要容纳道德上的正确性作为原则的效力条件;换句话说,至少存在一些原则,对于这些原则来说,其道德性是其作为法律原则的必要条件。这样一来,道德论证实际上起到了支持法律原则效力的作用,是其效力标准的一部分。问题在于,此种道德论证是在何种意义上进行的呢?这里争议在于,法律原则究竟是在个案事实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还是说它仅仅是在个案中因为特定的案件事实而获得了道德论证的支持。按照德沃金的看法,这种道德论证似乎是发生在个案裁判的法律推理过程中。这是说,就特定的个案事实而论,适用某项原则要比适用规则或另一项原则更具道德性,这种道德性因此成为该原则作为法律原则的效力条件。德沃金所反复引证的帕尔默案极易给人留下这种影响。由于原则具有分量或重要性的维度,在帕尔默案中,相对于其他可能适用的原则(例如意志自由原则),“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更具分量,借助这种论证,便可以判断该原则所具有的效力。然而,如果能联系法律体系的观念,德沃金的看法似乎有些太狭隘了。按照凯尔森的经典理论,法律规范的存在前提是另一个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在这一解释框架中,某项法律原则的效力受制于更高层次的另一法律规范。无非是,由于这里讨论的法律原则必须通过特定的道德论证,于是作为效力标准的高层次法律规范内容将出现类似的表达方式:“凡符合公平正义的规范是法律”。无论如何,一旦我们承认法律原则与体现这一原则的个案判决或个别规范之间存在区别,那么就其效力而论,法律原则只要经过了高层规范所规定的道德论证,就已经存在了,无需等到该原则适用至个案之中。在这个意义上,之所以能够认定法律原则的效力,不在于其在某个案件中符合某种道德论证,或是能够产生公正的判决结果,而在于,一个在先的效力标准支持了这些原则。这里的关键仍然在于,必须区分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和适用标准或认知标准。在类似帕尔默案这样的疑难案件中,法官的难题是如何适用法律,适用哪一法律的认识论难题,不是判断何为有效法律的本体论难题;在这种适用或认知过程发生之前,相关的法律原则便成立了,而这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与其是否应该被适用这一问题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否则,我们就难以主张一个法律体系中存在某项法律原则这样一个一般性的判断。
如果能够断定,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独立于适用法律原则的个案裁判,以至于法律原则效力在逻辑上先于对该原则的适用,那么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将更为清晰地呈现出来。当法官判断一项规则是否能够作为法律规则而存在时,其标准在于看它是否符合另一个特定的规则,例如系谱的承认规则;当法官判断一项原则是否能够作为法律原则而存在时,其标准在于看它是否具有道德性,由于这种道德性能够脱离一个具体的个案而存在,那么问题就变成了,如何论证一项一般性的原则具有道德性,这其实也就是要证成一项原则作为道德的效力。例如,对于“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来说,效力标准实际上要求法官作出论证,证明在道德上是成立,可以作为一项道德原则而存在,进而成为法律原则。问题在于,这种道德论证在多大程度上是所谓基于原则内容的,或是实质的,并以此区别于规则的效力标准?这里其实涉及到了一个伦理学或道德推理意义的上的问题,即一个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或条件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必也难以展开详考,但须重视此种情况:伦理命题有时也可以是基于系谱或来源的。就此,至少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人们之所以认定某个伦理命题是正确的,理由只在于它是全人类或特定社会普遍看法或实践。在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中,哈特曾通过区别实在道德(positive morality)和批判道德(critical morality)表达了类似的意思,而德沃金区分一致性道德(concurrent morality)与惯习性道德(conventional morality)的效果也是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道德本身实际上也是作为惯习而存在的。当法官判断一项原则是否属于法律原则时,表面看来,其效力标准在于它是否具有道德性;但此种道德性的标准又在于它是否获得了普遍的认可,或是形成了普遍的实践。
其二,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有时可以因为该道德标准是由某个权威所的。此种情况在宗教气氛比较浓重的社会中比较常见。在这些社会中,无论对于道德规范、法律规范还是宗教教义,其效力有无的标准都在于它是否来自于宗教权威,例如诸神的意志及其表达,宗教组织所的戒律等。当然,这种情况如果夸张到此种程度,即社会所有行为规范的效力标准都是同一个标准,那么也就很难主张这个社会还存在什么道德、法律或宗教之分了,本文所谓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效力标准问题也就不存在了。
在上述两种情况下,要判断一个道德命题是否有效,须考虑其是否是普遍共识或实践,或是考虑该命题是否是由某个权威所的。仅就伦理命题而论,其效力标准也是基于系谱或来源,而无需对伦理命题的内容加以实质的论证。于是,虽然作为此种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本身要求原则必须经过某种道德论证,但这里的道德论证过程所考虑的仍然是道德命题的系谱或来源,而非其内容。换句话说,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经由一个基于内容的标准,最终指向一个基于系谱或来源的标准。此时,这种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原则与基于来源的法律原则,乃至法律规则三者的效力标准,即便在性质上有所差异,但在形式或结构的意义上却极为相似,最终都将诉诸于原则的系谱或来源;无非是,确定此种法律原则效力的方式需要经过一个容纳道德论证的效力标准的允许。
当然,这里并不是要坚持,所有伦理命题的效力标准都是系谱或来源。在上述列明的情形之外,人们当然可以主张说,一项伦理命题成立与否,要对其内容进行实质的道德论证或道德推理。例如,我们可以论证说,“任何人不得从自己的错误行为中获益”这一原则是因为它符合功利主义这一基本道德原理而成为有效道德原则的。在这个范围内,德沃金本人对于法律原则效力标准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因而区别于法律规则的说法依然是可以成立的。
五、结语
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是多样且复杂的,既不能简单说它与法律规则效力标准一样是系谱的,又不能主张它完全是基于内容或道德论证的,与原则本身的系谱和来源毫无关联。实际上,某些法律原则的效力标准也是基于系谱的,而对于另外一些基于道德论证的法律规则来说,除了相应的制度支持之外,道德论证本身有时会指向系谱规则,并以此确定原则的道德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规则与原则的效力标准简单地归纳为系谱与内容的对立,其实质是加大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在本体论意义不必要的差异,将是难以成立的。
注释:
①〔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原理》,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页。
②张文显主编:《法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三版,第105页。
③④⑦参见〔英〕约瑟夫・拉兹:《法律的权威》,朱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130、128页。
⑤〔德〕石里克:《伦理学问题》,张国珍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99页及以下。
⑥陈嘉映:《语言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⑧⑩Jules Coleman, Authority and Reason,in The Autonomy of Law, edited by R. P. George, 1996,Clarendon Press, P291,293,287.
⑨H.L.A. 哈特:《法律的概念》(第二版),许家磬、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1、237页。
Ronald Dworkin, “Models of Rules I”, in Taking Rights Serious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 p. 39,22,22,53.
篇(7)
1.法律原则的概念
法律原则是法律的基础性真理或原理,为其它规则提供基础性或本源的综合性规则或原理,是法律行为、法律程序、法律决定的决定性规则。此为布莱克法律辞典的解释,对于法律原则亦有中国法学教授对此作出定义,如张文显教授对此的定义为法律的基础性真理、原理,或是为其他法律要素提供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原理或出发点。根据此定义不难看出,法律原则在法律要素中所占的基础性位置,在法律原则中存在着较为抽象也是较为基础性的原则,例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公平原则,各个部门法中也有自己相应的法律原则。
2.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
法官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适用的多为法律规则,这是由于规则具有明确性,可实施性、可操作性,而法律原则则比较抽象笼统,不利于法官案件的审理。法律原则虽然有其自身的弊端,但是,现代法学中,法律原则仍可运用于案件审理中,而且,就目前情况来说,法律原则适用具体案件审判仍为数不少。这是因为法律不是万能的,而法律规则有他的滞后性和僵化性,单纯依靠法律规则审判案件,就会造成个案的不公正,为实现个案正义,法律原则的运用就不可避免。它会在整体正义的框架中,弥补法律规则之间的漏洞,化解法律规则的僵化性,实现个案正义,因此,实现个案正义是法律原则直接适用于案件审判的最终目的。
现今,通说认为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有以下三点:
2.1穷尽法律规则,方得适用法律原则
“穷尽”在此,笔者认为应表现为两个方面,即“穷”和“尽”。“穷”是指法律在此方面本无规定,不存在具体的法律规则。这是由于法律不是万能的,法律不可能穷尽一切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社会现象,对此,社会中一定有某些领域是法律所遗漏的,是其尚未覆盖的,因此当法律对此方面没有具体规则适用时,未解决法律纠纷,实现个案正义,就可适用法律原则。例如:贾国宇诉北京国际气雾剂有限公司、龙口市厨房配套设备用具厂、北京市海淀区春海餐厅人身损害赔偿案,该案在审理时,我国尚未存在精神损害赔偿,但法官适时使用法律原则,在判决时认定“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的原则和司法实践掌握的标准,实际损失除物质方面外,也包括精神损失,即实际存在的无形的精神压力与痛苦。本案原告贾国宇在事故发生时尚未成年,身心发育正常,烧伤造成的片状疤痕对其容貌产生了明显影响,并使之劳动能力部分受限,严重地妨碍了她的学习、生活和健康,除肉体痛苦外,无可置疑地给其精神造成了伴随终身的遗憾与伤育,必须给予抚慰与补偿。”由此,精神损害赔偿在中国予以确立。此为法律原则成功适用的典型案例。“穷尽”法律规则另一面就体现在“尽”,即法官在审理案件是已尝试使用了在此方面全部的法律规则,仍不能实现个案正义,则可适用法律原则。
2.2一般不得舍弃法律规则而直接适用法律原则
法律需要绝对的权威性,任何人、机关、社会团体都不得干预法律的实施,但法律如何保证权威性,就其自身而言,法律本身应保证其稳定性,若法律自身朝令夕改,就会大大降低法律的权威性。法律原则虽然对法律规则有指导性,但其自身灵活、抽象,若法官任意使用法律原则进行审案,就会加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然而由于法官个人水平的差异及对法律驾驭能力的不同,就会降低案件的稳定性,长期以往是对法律权威性的极大破坏。因此,笔者认为“不得舍弃法律规则而直接适合法律原则”是十分必要的。
2.3没有更强理由,不得径行适用法律原则
在这里所谈的没有更强的理由,不得径行适用法律原则,笔者认为是对第二个条件的加强补充,目的也是不可轻易使用法律原则审判案件,也就是第三个条件实与第二个条件为一个内容。
笔者认为,法律原则在许多案件的审判过程中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决了许多疑难案件,例如美国有名的黑格斯诉帕尔默案[],上文提到的贾国宇人身损害赔偿案,在这些案件中,法律原则的成功适用,使案件得到了顺利解决,并且案件最终的审判结果也为多数人认可赞同,但是,也有个别案件在审理过程中运用法律原则,但得到的结果却褒贬不一,例如:泸州遗赠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就是根据公序良俗原则,未支持原告张学英的诉讼请求,此判决一下就引起多方争议,持反对意见的人认为,张学英持有的遗嘱合法有效,此判决若根据《继承法》的具体规则进行审理,张学英必然胜诉,然而法院舍规则适用原则,本身不符合法律原则适用的条件“穷尽一切法律规则”,对案件结果不予赞同。对于法律原则在案件审理中所出现的问题及法律原则适用条件的规定来看,笔者认为:应将法律原则的适用条件简化为两条,一是“无法律规则规范的情况下,适用法律原则”,二是“无争议的实现个案正义”。
案件审理按法律规则的有无可分为两种情况:有法律规范可以适用和无法律规范适用。当无法律规范适用时,使用法律原则无可厚非,而且法律原则符合法律追求的根本目的“公平正义”,案件审理的结果也会为多数人认可。对于笔者所说的第二个条件“无明显争议的实现个案正义”就是在有法律规范的前提下,若要舍规则就原则,则要保证“无明显争议”。在此所提明显差异是为了在适用法律原则时,法官应本着慎用的原则,不可轻易举起“实现个案正义”的大旗就舍弃规则,因为对于正义的理解人与人有认识的差异,在这种使用规则会引起争议、使用原则也会引起争议的情况下,就不能轻易的使用原则。此可以维护规则的稳定性和权威性,这也就维护了法律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减少个案之间的差异。
结论。综上所述,法律原则在案件审理的使用条件,应本着无规则则可无条件的适用法律原则,若有规则对其进行适用,则本着谨慎适用原则,尽可能的适用规则而尽量避免适用原则,尤其是在使用原则会引起争议、使用规则也会引起争议的情况下,就更不可适用原则,而应使用规则,以维护法律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篇(8)
在《国际商会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海事仲裁机构规则》中第10条规定:“当事人自己决定仲裁员适用争议是非曲直的法律。在当事人对缺乏任何指引时,仲裁员应适用他自己认为适当的冲突法律规则所指引的适当法。”该条实为《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28条的体现。各国在立法中均援引了该条所确立的精神。
虽然在现代某些国际商事、海事仲裁规则的规定中,为确保仲裁案件适用法律的合理性而规定了仲裁庭首先找出应适用的冲突法律规则,然后再根据冲突法律规则的指引决定应适用的实体法律,但在实践中,首先由仲裁庭自己决定选择哪一国的冲突来规范,然后再通过该国冲突来规范指引以决定法律适用程序已早就让位于根据国际上公认的冲突规则-与争议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而直接选定适用某国的实体法以解决案件争议问题确确实实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然而,作为一项法律适用原则,还是有必要对仲裁庭究竟应该根据什么理论或原则来选择何国的冲突规则作一番简单阐述。
1.仲裁地的冲突规范。
传统的国际海事仲裁中,依据仲裁地的冲突规范以确定争议实质事项法律的适用是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的一种最普遍、最基本的方式,即使在现代,依仲裁庭或仲裁员认为合适的冲突规范来决定实体法律的适用已在理论上被众多的国际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或国际公约所采纳,但“仲裁庭认为合适的冲突规则”虽然并不总是,但却常仍旧是仲裁地的冲突规范。
2.适用与仲裁程序法相同的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
因为国际私法也是程序法,仲裁员故常适用与仲裁程序法相同的国家的国际私法以决定案件实体法律的适用。除了适用仲裁地的冲突规范和与仲裁程序法相同的国家的国际私法规范以外,仲裁庭用以决定实体法律规范而可以适用的冲突规范还可以是仲裁员本国的国际私法,在临时仲裁的情况下或独任仲裁员的条件下有可能出现;裁决将被被执行国的冲突来规范;与争议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冲突来规范等等。但无论适用那种冲突规范,都不如直接适用实体规则或根据国际上公认的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而直接确定实体法律的适用更为实用。因此这里不在对适用冲突规范以决定实体法律的问题多作探讨。
中国海事委员会的仲裁规则中没有明确法律适用条款,当然也就更谈不上在当事人未作法律选择时,仲裁庭首先决定适用那一国的国际私法规则,然后据此指引再决定实体法律的适用问题了。在实践中,仲裁庭总是采取最直接最实用的方法,即根据最密切联系原则找出合同应适用的准据法以解决案件争议。
(二)直接适用国内法律
1.直接适用某一国家的实体法律。
直接适用某一国家的实体法律实际上就是直接找出合同的准据法。而直接找出合同的准据法在当代最为流行的就是通过合同的一系列联结因素,如合同的缔约地履行地合同当事人的居住所地营业地法人登记地等,包括仲裁地,从中找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法律,以此作为合同的准据法。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作为一项法律适用原则已广为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接受。
在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实践中,从理论上来说,倘若当事人没有在合同中规定应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在争议发生提交仲裁后也没有就争议应适用的法律达成一致意见时,仲裁庭将直接依据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与争议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但实践中,至少到目前为止,这样的案例还很少,因为在许多情况下,当事人在合同中对许多问题都有明确的规定,仲裁庭只需要根据合同规定即可对争议问题作出正确的裁决。
2.直接适用公认的冲突规范指向的国家的实体法。
对一些具有共识的法律适用问题,仲裁庭可直接适用公认的冲突规范指向的国家的实体法律。所谓“具有共识的法律适用问题”以及“公认的冲突规则”,作者这里指的是如“侵权适用侵权行为地法”、“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等这样一些冲突规则。这种冲突规则已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认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对此均作了同样的规定,因此,在遇到上述争议事项时,就不必考虑适用哪一国的实体法律而直接适用这些“公认的冲突规范”指向的国家的实体法律。
在国际海事仲裁案件中,由于受国际公约的影响,各国的法律制度中有关共同的法律原则就更为普遍,这就为仲裁案件中的实体法律适用问题带来一定的便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十四章关于“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中,除第168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以及第269条关于“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合同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之外,其余有关海事海商方面的法律适用问题规定,应该说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即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有关规定或者与有关的国际公约的规定都是较一致的。
(三)适用非国家制定的实体法律规则
与仲裁程序法的非国内法的趋势一样,仲裁案件实体法律适用超越国家之外而适用国际法、一般法律原则和国际商法的情况已绝非少见。现今之主要学说与实践认为,既然仲裁制度的主要特点是允许当事人有选择法律的自由,则就没有任何理由限制当事人只选择国内法而不选择国际法以及基于公平和善意原则作出的裁决。
1.根据国际法和一般的国际法惯例选择适用法律。
与国际海事有关的国际条约是缔约国之间解决国际海事争议的首要依据。因为国际法的一项古老的原则就是条约必须守信,所以当一国参加了某个国际条约,就必须承担执行该公约的义务;而当其国内立法与该国参加的国际条约的规定相抵触时,除非该规定为该国声明保留,一般应以该规定为准。
篇(9)
(一)国际私法的定义应为有前提的特称命题
国际私法具备国际法属性这一命题的前提是在当代国际关系日趋发展、国际法主体日益增多情况下,法人、自然人间涉外民商事关系亟待国际法的调整。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笔者论述的命题似乎不是一个全称命题,而系特称命题。需要指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称命题是不存在的。不仅在社会科学领域如此,在自然科学领域亦然②。若要强调“国际私法具有国际法属性”这一命题在时间上全称成立,则需要论证国际私法在13、14世纪诞生之初即具备国际法属性,这一点已由学者著文论证,这里不再赘述[2]97-104。既然以语境为前提论说命题,那么我们还需了解在当今世界,国际法调整的国际关系的内容已然极大丰富。目前认为广义的国际关系是“国际社会中的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主体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按一定的准则,有规律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统一体”[3]225。也就是说这种丰富主要体现为主体种类的增加。由此,国际关系除了国家之间的关系外,又包括了不同国家及地区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关系。而国际私法调整的对象是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显然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形式,可以说在这个层面,我们就可认为国际私法现在、将来均具有国际法属性。国际私法属性这一命题的核心即事物的性质,是对其内涵的高度概括。
(二)国际私法
国际私法包含了冲突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国际民商事争议解决规范(含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及其他争议解决办法等)③;而冲突法包括了系属、准据法。国际统一实体私法的国际法属性。统一实体法律规范,表现为国际条约、公约。无论是国际公法学者还是私法学者对于国际条约的国际法属性大多不存异议。显然,从效力根据上看,旨在调整不同国家(法域)民商事主体之间民商事法律关系的国际条约(公约)也应当是“各国意志相互妥协”的产物。《国际法院规约》第38条中列举的国际法渊源本也包括了各类契约性和造法性的国际条约④,这也是令国际公法学者对其国际法属性产生信服的证据。随着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在国际私法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国际私法就愈发具有为公法学者所认同的所谓“国际法属性”。
冲突法的国际法属性———从其效力根据着眼。习惯催生了法律。而广义的习惯存在于社会横向、纵向的发展中,如哈耶克所言:“习俗和传统比理性更久远:习俗和传统是处在本能和理性之间,无论从逻辑上、心理学上还是时间顺序上说都是如此……通过学习得到的道德规则和习俗日益取代了本能反应,但这并不是因为人利用理性认识到了它们的优越之处,而是因为它们使超出个人视野的扩展秩序之发展成为可能,在这种秩序中,更为有效地相互协调使其成员即使十分盲目,也能够养活更多的人口并取代另一些群体。”[4]21故而在我们将各类规则习惯做“入法”尝试时,以具弹性态度审视就显得尤为重要。冲突规范传统认知面临的挑战。国际私法的核心是冲突法。冲突法是冲突规范的集合。而对于冲突规范的国际法属性是学界争议的焦点。国际公法甚至不少国际私法学者之所以认为冲突规范缺乏国际法属性是从规则调整的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因素着眼。以戴西(Dicey)为例,他在《ADigestoftheLawofEnglandwithreferencetotheConflictofLaws》中的第一章中就指出,他反对以国际私法来命名冲突法的原因在于“它的使用与其在‘国际法’这个表示调整国家之间关系的法律术语中的正常含义很不相同”[5]27。
在戴西看来,国际法之“国”即国家。国际法即调整国家之间权利、义务之原则、规则、制度之总称。但戴西的观点面临着两方面挑战:一是现实挑战。在戴西生活的时代,人们在描述不同法域适用冲突规范的情形时用“国家”(country)甚至“国家”(state)代称法域了。虽然戴西及其著作修订者莫里斯(Morris)将此情况视之为仅仅是一种“技巧术语的运用”。但习惯用法的背后其实是对各法域(或自治权)存在的承认;二是时代挑战,随着国际关系日趋向复杂化方向发展,国际法的内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国际法的主体不再限于国家,国际组织、法人乃至个人都有可能介入涉外事务中。传统的“国际法=国际公法”的观点已显得不合时宜。以个人、法人为主体的国际私法成为国际法下属之部门法是符合当前国际交往的需要的。从冲突规范效力根据证明其国际法属性。纵然我们以“意志间的相互妥协”这一实质渊源作为标尺考察冲突规则,我们也可以发现:“在重大案件中,个人利益不能轻易的和国家利益相分离。”[6]
事实上,为各国所遵循并践行的传统冲突规范⑥已经具备了国际习惯法的特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意志间相互妥协”的产物———公平给予各法域法律以适用机会———这种对于各法域来说可期待实现的司法利益恰是意志(或者授权下的法域自治权)相互协调的结果。虽然戴西和莫里斯强调国内适用外国法并非出于礼让或是互惠的需要,但事实上,基于维护并促进国际民商事往来的愿望,各国均在法律适用、管辖权方面做出让步⑦。国际私法实践已经证明,冲突规范不仅是各国(法域)的重复的类似行为,而且是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行为。它已具备了成为国际习惯的条件。由冲突规范中连接点指引出来的准据法,究其本质,乃是各国的国内法,但由于被赋予了公平适用的机会,则具体民商事法律关系适用的可能是外国法,这就使得抽象意义上的准据法具有涉外性。从历史上看,域内法具备域外效力也是国际私法产生的前提。更为重要的是,一俟认定冲突规范为国际习惯,则通过冲突规范中连接点指引确定准据法(特定实体法规范)适用视为国际习惯运用。
至于为什么冲突规范大多存在于各国国内民商法之中,我们可以把这种现象看做各国对通行于世的、约定俗成的习惯、原则的适用,正如“地之上下之物皆归地之所有者”的罗马古谚未见诸于国际成文立法之中,但却为各国物权立法所接受的那样。冲突规范系法律原则而非技术性规范。法律规范包含法律规则和法律原则,而并非所有法律规则里面法律规范的三要素均齐备,法律原则更是如此,只要其内容对法律主体间权利义务做出规制即可。如上文所述,冲突规范作为一种原则性的国际习惯,其逻辑结构虽与典型法律规范有异,但它给予各国民商法以调整具体权利义务关系的平等机会。它决定了各国法的适用,也就决定了民事主体间权利义务的调整。从调整涉外民商事法律关系全过程着眼,冲突规范作为原则的指导性作用发挥的十分明显,这种作用是技术规范所难以做到的。
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等民商事争议解决办法的国际法属性。如前所述,在不同国家的民事交往中,为了建立相应的秩序,需要有明确的交往规则来确定行为人的权利义务,国际私法因此而产生。所以,国际私法的目的和任务从一开始就是要解决或确定国际民商事交往行为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以此来建立和维护一种合理的国际民商事交往[7]。至于采用法律选择的直接方法还是间接方法来调整,则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的国际私法的发展状况,而不影响国际私法的目的和性质。民商事交往的扩大、深入促进了秩序的扩张,否则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将难于得到确定、保障。典型的例子便是民事诉讼、商事仲裁制度被引入国际民商事争议的解决中。调整对象性质的变化决定了相应法律规范性质的转变。民事诉讼、商事仲裁关系中涉外性的出现决定了调整此类关系的国际民事诉讼法、国际商事仲裁法的国际法属性。
国际私法各组成部分中,统一实体法律规范具有国际法属性已然为公私法学界所认可。依据“法律规范的性质由其调整对象性质决定”这一观点,国际民事诉讼与商事仲裁的国际法属性亦可得到证明;而作为国际私法核心的冲突规范,因效力根据源于“意志间相互妥协”,广义上可认定为国际习惯,所以通过冲突规范连接点指引出的各国民商法的适用过程应视为国际习惯的具体实践,则从总体上看,冲突法即具有国际法的属性。则概括起来,国际私法整体上具备国际法的属性。
二、自卡弗斯“优先选择原则”展开
在现代,国家之间交往方便而频繁,国际习惯有可能在较短时间内形成。这种“即时”国际习惯法,其重点在于“法律确念”,而不在于“常例”[8]。一些具有革新意义的学说亦可在加入冲突规范体系后,成为国际习惯,而被注入了新规范内容的冲突规范也将可以应对日趋复杂的涉外民商事关系的调整需要。不少国际私法学者也强调冲突规范改进的重要性。“一切值得尝试的方法,贴着或同或异的标签,都在以往被尝试过了”[9]。卡弗斯就指出:“规则形成之后,规则的适用并不妨碍对其本身继续探索下去。机械的规则极大地限制了与适用规则有关的事实的审查范围。对那些容易机械处理的问题而言,运用机械的规则才是合理的。在法律选择案件中,已经形成的规则必须含有可变因素,用来容纳本质上不可预料的复杂情况”[10]。
事实上,传统的立法管辖权选择过程要求法官选择某个国家的法律,用来作为案件的准据法,而不必顾忌该法的实体内容。其局限在于:法官做出法律选择的过程常常是盲目的,所选择的法律可能根本不利于具体的实体争议的解决;法律选择的依据常被认为是“机械的、武断的”;法官不得不依赖于识别、公共秩序、反致等例外规则来逃避做出不合理的法律选择,这却又增加了判决得不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风险。面对法律选择规则日渐僵化、不合理的现实,卡弗斯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法:在法律选择的过程中,法院必须从实体上对被选择的法律规则做出审视,具体来说:“法院面对该问题,应该仔细审查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引发争议的交易或事件;认真比较可适用的法律规则和法院地规则(或者其他竞相适用的法律),以及比较它们各自适用于案件时产生的结果;根据使事件或交易和某个法律发生关联的某些事实来评价上述结果,评价应从维护诉讼当事人之间的公平出发,顾及法律冲突可能引起的更广泛的社会政策问题。”[11]10
篇(10)
对法律体系的研究,实则分为对法律内在结构的研究和对法律外在结构的研究。对法律内在结构的研究,一般体现为对法律规范自身的构成分析。对法律外在结构的研究主要体现为对一个国家立法体系结构的研究。这一研究又可以从部门法划分、法律形式、法律规范、法律效力等不同角度进行。[1]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大多数国家信用总规模超过GDP的增长,经济主体都更普遍地采用信用方式与信用手段进行融资和支付结算,各种各类主要信用工具都与GDP有极强的相关性,信用对经济的作用与影响不断扩大;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大量投放信用工具,[2]50%的企业赊销比例超过3/4,市场上信用经济的比例接近或超过50%,消费者个人信用消费也呈快速增长趋势,[3]2009年,我国的贷款数量高达9.6万亿人民币,我国正在步入信用经济社会。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是,通过对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发现,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存在的结构性缺陷影响着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建设。
一、结构虚空与效力软约束
发达国家经过百年的信用制度建设,形成了覆盖广泛的信用体系的完整架构,其健全的法律法规成为征信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完善的标志。[4]1996年,我国国内市场全面转入买方市场,一些企业开始赊销,市场需要为各类“授信人”创造适应信用交易活动的环境。在这种背景下,1999年8月,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正式启动,[5]与此相适应,我国陆续制定、颁布与信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开始了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建设。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由社会信用基本元素(即企业信用、银行信用、个人信用、政府信用[6])、信用活动及其法律制度构成,它们共同指向的对象即是信用本身。[7]
我国社会信用法律来自不同的立法机构(政府部门),这些法律如何形成一个完整的社会信用法律形式体系?在这个体系内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和规定关系如何?判断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完整性的标准是什么?关于法律形式体系,哈特建立了由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组成的具有等级性的规则体系。凯尔森建立了由基本规范为终极效力的承认规则体系。凯尔森认为,在一种法律体系内存在着多种形式的法律和不同级别的立法机关,体系内的法律是被主要机关所承认的法律,[8]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有效链”,有效链就是这样一种规范:第一,每一种规范都被授权只能产生本体系内的另外一种规范,除了那些本身没有被授权创造规范的之外。第二,每一种规范的产生都只是其他一种规范行使权力的结果,除了那些未经本体系内任何一种规范授权的规范。[9]凯尔森有效链反映两方面内容,一方面是一个法律体系内的成员标准,另一个方面是在每一种法律体系内,法律之间都会有一种生成关系。
首先,一个法律规范如何才能构成一个法律体系的链条环节。奥斯丁、凯尔森都提出了体系成员的身份标准或成员资格标准。按照凯尔森的理论,成员的身份标准是:当且仅当一个法律是通过被基本规范授权的权力实践所创造,而这一基本规范也授权权力机关创造所有其他的法律,这个法律才具有特定体系内的成员资格。[10]更具体地说,凯尔森的成员身份标准是这些法律规范的来源,它们都能够通过立法者的权力指向找到体系的归属。按照立法者权力作为成员划分标准,我国法律形式体系由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规章、部门规章构成,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也必须遵循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政府部门规章的形式体系结构。但是,凯尔森的论断只能说明成员身份的来源,却不能说明成员本身,因为每一个法律规范或者说不同形式的法律都是一个独立的内容单位,都发挥着特殊的法律效力,都反映不同的社会形态。按照拉兹的观点,“在一种法律体系内,不同种类和不同模式的法律之间的内部关系最终依赖于两个因素:(1)个别化原则;(2)法律体系内容上的丰富性、完整性和多样性……个别化的原则使得某种形式的内在关系之存在成为可能,而体系的复杂性则决定着这种内在关系是不是真的存在于该体系之中……当且仅当一种体系具有高低限度的复杂性时,这种规范性体系才是法律体系。”[11]由于法律内容的多样性和个别性,仅从立法者的角度出发(或者仅从法律规范来源的角度出发)难以认定同一立法者颁布的法律就构成一个法律体系,因而法律体系内成员身份标准的认定应该增加不同法律规范的共同指向标准。社会信用法律虽然由不同元素构成,但是它们共同指向信用,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成员身份或特性依赖于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所属的社会生活形态,调整信用的法律规范作为一个独立的内容单位,它们构成了社会信用交易的行为理由。作为个别化原则的信用构成了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成员本身的一个特质,因而,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构成标准也是来自社会信用法律的内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法律的效力。可以认为,我国社会信用法律特质能够使信用法律构成相对完整独立的自治体系,这一体系在体系构成与效力来源方面与我国法律体系具有自我相似性。或者这样认为,法律体系本身是一个母系统,它由若干子系统组成,[12]社会信用法律体系是我国法律体系的一个子系统。
其次,如何判定法律体系内的生成关系?哈特法律体系理论建立在规则结合的基础上,即法律体系是由第一规则(或称初级规则)、第二规则(或称次级规则)和承认规则组成并由此产生法律规则的生成关系,规则与规则之间的生成是通过承认(接受)或服从来实现的。[13]按照凯尔森的观点,法律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形,低级法律规范的效力来自高级法律规范,而全部法律规范的效力都来自于宪法这个最高规范。[14]在我国的立法实践中,法律的形式体系是根据我国的立法法,构建了以宪法为最高指引,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政府规章、国际条约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这一法律形式体系按照逻辑规则构成了法律效力层次并形成了我国法律位阶制度。[15]
在我国法律体系内,法律之间的生成关系体现为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所有的法律在宪法中都应该找到确定的条款指引。宪法的地位和作用是构成法律体系的最高效力来源。然而,作为法律体系生成最高指引的我国宪法却不能为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提供有效的指引和基础来源。宪法作为根本大法,具有纲领性文献的作用,不可能对国民经济、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出详细规定,但是,一个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社会信用体系“是一种新的社会机制,作用于一国的市场规范,旨在建立一个适应信用交易发展的市场环境,保证该国的市场交易形式向信用方向转变,即实现从以现金支付手段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向以信用交易为主导的市场交易方式的健康转变。因此,社会信用体系将在中国市场上建立一种新的游戏规则,既要保证市场上各类商业和金融信用的大规模且公平地投放,又要保证授信人取得高的授信成功率”。[16]信用在经济社会的重要作用凸显我国建立社会信用法律体系的迫切要求,信用法律体系的生成需要宪法的指引。目前,我国宪法没有专门的条款对社会信用的问题做出规定,宪法中一些与信用相关的条款如保护人权、保护社会主体财产权利、国家预算职能与审计监督规定主要体现在《宪法》第38~40条、[17]第62条第10款、[18]第85条第5款、[19]第91条。[20]考察信用经济社会的法律需求,在社会信用法律制度体系建设的宏观与微观层面,我国宪法显然不能提供重要的规范与指引。
作为我国法律形式体系中第二层次的法律,应该成为社会信用法律的重要生成依据。但是,目前,我国社会信用法律体系基本法律供应不足,缺少核心的专门法律规范,大量部门规章的生成没有基本法律的指引,法律体系生成存在障碍,形成社会信用法律结构的虚空,导致社会信用法律效力示弱。
第一,个人信用法律子域体系。个人信用是社会信用的基础。[21]在发达国家,个人消费信用已经成为信贷市场的主体,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一般可达60%左右。我国的消费信贷已进入市场高速成长期,其市场规模平均每年以160%的速度增长,占GDP总量的10.46%。[22]从1999年至今,我国先后出台了《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住房置业担保管理试行办法》、《助学贷款管理办法》、《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规定》、《信用卡业务管理办法》、《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规范个人信用的行政规章制度。如果以征信国家发达的法律制度供给为参照比较对象,[23]我们发现,我国没有一部专门针对个人信用的如消费者信用法、信息自由法、个人隐私保护法、个人数据保护法等基本法律法规;已经颁布的上述规定缺少基本法律层面的法律生成依据和效力支持。
篇(11)
关于提单物权关系的准据法,在国际私法上向来也有两种不同见解。一种为“分离说”,即认为提单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应适用不同的准据法,提单的物权关系应依“物之所在地法”决定。另一种为“统一说”,即认为若将提单法律关系分割为二,各有不同的准据法,适用上非常不便。提单的物权关系依从于债权关系而存在,因此其准据法应和债权法律的准据法相同。就实务而言,采用“统一说”比“分离说”方便;但从理论上而言,提单的物权关系和债权关系是分别独立的两种法律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有从属关系并无依据。如果采用“分离说”,国际私法上最常用的原则是“物权依物之所在地法”,但运输途中的物是移动的,在发生某种物权法律关系时,很难确定货物正通过哪个国家,即使能确定,这种关联完全是偶然发生的,是有关当事人无法预料的,因此也是不尽合理的。所以有学者认为由于运输途中的货物终极目的地是送达地,对在途货物进行处分行为,一般也要等到运输终了,才会发生实际后果,以交货地法确定运输途中货物物权关系的准据法较为合理。笔者基本上同意“分离说”的理论,但运输终了未必是交货地。所以仍应以“物之所在地法”为原则,在物权行为发生地无法确认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再以“交货地”、“货物扣押地”等为连接点确定货物物权关系的准据法。
提单的法律行为主要包括提单的签发、转让和注销。各国法律对此规定也是有所不同的。在提单的签发上,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人的签名可用盖章来代替,有的国家法律规定法人签名必须是法人代表手签;在提单的转让上,我国法律规定“记名提单:不得转让”,但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的法律均规定,记名提单可以背书转让。这样提单的法律行为是否有效有赖于法院地法对提单行为准据法的选择。按照传统的国际私法的“场所支配行为”原则,法律行为的效力适用行为地法。晚近发展的国际私法摒弃了那种固定的连接方式,而是采用了多种连接因素,以更为灵活、弹性的方法,来确定法律行为的准据法。如1946年《希腊民法典》第11条就规定:“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决定行为内容的法律,或者符合行为地法,或者符合全体当事人的本国法,皆认为有效”。同样,提单法律关系中的有关当事人在签发、转让提单时当然也是希望其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有效的,此外提单的流动性很强,其效力在整个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对提单的法律行为的效力的法律适用也要尽可能采用积极、灵活的方式。比如可以采用选择式的冲突规范,规定:“提单法律行为的方式如果符合提单债权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或者符合提单行为地法,或者符合任何一方当事人的本国法,或者符合法院地法,皆认为有效”。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得知提单债权关系的准据法一般并不适用于提单物权关系和提单的法律行为的效力。这是我们在解决提单纠纷案件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在以下讨论的提单法律适用原则及其序列仅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因为几乎所有国际商事合同的法律适用原则都能适用于提单的债权关系,同时由于提单的特殊性,又使得这些原则在适用提单债权关系时又有独特的表现。而提单的物权关系和提单法律行为效力的法律适用相对而言就比较简单,本文就不再作展开论述了。因此在下面的讨论中,笔者所言及的提单的法律适用和准据法实际上指的是提单债权关系的法律适用和准据法。
法院在解决提单法律适用问题时,通常会提及某些“原则”,但提单法律适用究竟有多少原则应该遵循,它们适用的先后序列又如何,这方面的探讨并不多见。虽然每个国家或是不同的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或不是任何有关提单的国际公约的缔约国,同时他们的国内法律规定的国际私法规范也不同,不是什么原则都能适用。但各国在采纳提单法律适用的原则上还是遵循了一定的规律。本文拟探讨大多数国家都能适用的提单法律适用原则的序列以及这些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原则
一般海上货物运输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涉外法律都会有专门的条款规定本法的适用范围,如波兰海商法规定,本法是调整有关海上运输关系的法律;我国《海商法》第二条也相应规定了本法的适用范围。但这些条款都不是国际私法意义上的法律适用条款,也即它并没有规定那些案件必须适用本法。但也有国家直接在本国海上货物运输的法律中用单边冲突规范的形式规定了法律适用规范,其中主要是由于某些参加国际公约的国家,为使公约生效,将公约的内容列入各自的国内立法,在二次立法的过程中,往往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对其法律的适用范围作出不同于公约规则本身规定的法律适用范围的强制性规定。
如澳大利亚1991年COGSA第11条规定:“提单或类似所有权凭证的当事人,凡与从澳大利亚任何地点向澳大利亚以外的任何地点运输货物有关的,……均被视为是有意按照起运地的现行法律订立合同的。”因此,从澳大利亚出口的提单和其它单据,只能适用该国法律,从而排除当事人选择适用其它外国法律或国际公约。英国1924年COGSA第1条亦规定,除本法另有规定的外,以英国港口为航次起运港的所有出口提单均适用该法。英国1971年海上运输法亦相应地把原来只管辖与适用出口签发的提单的条款改为也适用进口。最典型的是美国1999年的COGSA(CarriageofGoodsbySeaAct),该法明确规定,对外贸易中作为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据---提单或其它权利单据受本法的约束。关于其强制性,通过这样一个事实就可见,即世界各国的许多班轮公司在其经营美国航线的班轮运输的格式提单上专门列有地区条款(LocalClause),规定对于运自美国的货物,提单的条款受美国的COGSA约束。中远的提单也不例外,其背面条款第27条就是LocalClause。当然,美国COGSA的这个强制性法律适用规定,只在其本国发生诉讼时具有强制性,因为它毕竟是一国的国内法,班轮公司之所以要制定这样的地区条款,是为了使进出美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纠纷案件即使不在美国行诉,也能用同样的法律解决提单的纠纷,因为其它国家不一定有这样的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而可能遵循意思自治原则,因此可保证这类业务所引起的纠纷在法律适用上的一致性。除美国外,这类国家还有比利时、利比里亚、菲律宾等。在这些国家,只要外贸货物运输是进出其国内港口的,提单就须适用其国内法化的海牙规则,而不论提单签发地是否在缔约国。
因此这类国家法院在审理以上所言及的法律所规定的某些案件时,是直接适用这些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国内法,一般是排除当事人的选择和其它法律适用原则的,因此具有强制性,这也是本文将这类规范命名为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的原因。
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法律被称为“强制性规则”,当事人是不能通过任何手段排除其适用的,对于某些案件,内国的国家将直接适用“强制性规则”,而不考虑当事人的法律选择。因此“强制性规则”在法国等国家通常又被称作“直接适用的法律”
此外,这类国家在依据所缔结或加入的国际公约制定内国法时,同时也是在履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因此制定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并没有违反公约的规定,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国际公约的适用范围。
二、缔约国的法院优先适用国际公约原则
关于提单的三个公约均是实体法性质的国际公约,公约既然是国家制定的,按照“合约必须遵守”(pactasuntservanda)的原则,缔约国负有必须实施其所缔结的国际公约的责任。缔约国在其域内实施其所缔结的统一实体法公约,在许多情况下都意味着缔约国的法院必须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适用该国际公约。但是也有例外,某些国际公约规定合同当事人可以全部或部分排除该公约的适用,如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中有这样的规定。但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没有“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条款,在法律效力上,属于强制性的国际统一实体法规范,缔约国的法院有义务对符合公约适用条件的案件优先适用公约,也即这种情况下,缔约国的法院是排除当事人选择的其它法律的。1983年的“Morviken”一案就是如此,在该案中,货物是装在一艘荷兰的货船上,自苏格兰的一个港口起运,提单上是注明适用荷兰的法律,并且阿姆斯特丹的法院有管辖权。但本案的货方在英国法院提讼,英国是《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缔约国,而且本案符合该公约的适用条件,(货物从一缔约国起运,提单也是在一缔约国签发)。本案若适用荷兰的法律(荷兰当时还没参加《海牙—维斯比规则》,适用的是1924年的《海牙规则》),则降低了承运人的责任。因此本案以该理由驳回了承运人主张中止诉讼的请求。结果,承运人依《海牙—维斯比规则》进行了赔偿。
但这项原则的适用仍是有例外的,《海牙规则》和《海牙—维斯比规则》的第五条都规定:“承运人可以自由地全部或部分放弃本规则各条中规定的全部权利或豁免,或其中任何部分,或增加其所应承担的任何责任与义务。但是这种放弃和增加,需在发给托运人的提单上注明。”众所周知,就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而言,《海牙—维斯比规则》比《海牙规则》重;《汉堡规则》比《海牙—维斯比规则》重。因此对于本应适用《海牙规则》的提单,当事人同意《海牙—维斯比规则》或《汉堡规则》或其它承运人的责任和义务较重的国内法的,那么后者的规则中增加承运人的责任与义务或减少承运人的权利与豁免的条款一般应予以适用。当事人若在提单中直接规定了增加承运人责任与义务或减少其权利与豁免的条款,尽管与应适用的国际公约冲突,也是应被采纳的,因为公约本身进行了这样的规定。当然大多数承运人已在其格式提单中对这一情形进行了排除。如日本一航运公司在其提单背面规定“…如果其它任何国家的法令被判定适用,则本提单受该法令条款的约束,在此法令下,本提单任何内容并不认为是放弃公司的权利和豁免权或对其责任和义务的增加。如果本提单的任何条款与上述法令或法规的规定不一致,这些条款将无效,但不影响整份提单的执行。”
由于种种原因,目前关于提单的三个国际公约是同时并存的,有不少国家同时是几个公约的签字国,目前这种混乱的状况还难以消除,公约本身也未对这种情况下,公约应如何适用作出规定,不过,各缔约国一般都通过制定国内法加以解决。有的将国际公约转为国内法,对涉外贸易中进出本国港口的海商案件强制适用指定的国内法,如美国;也有的采用双轨制,对来自《海牙规则》国家的货物实行《海牙规则》,对所有出口货物则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如法国。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原则与缔约国根据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而适用本国法并不矛盾,因为这些国家在适用国内法的同时也同样在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只是这些强制性法律适用条款将导致某些根据公约规则本身的规定并不适用公约的案件,事实上也适用了公约,而且是强制性的。正因为如此,强制性法律适用规范所指向的内国强制性规则最为优先原则在顺位上应列在第一。
三、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协商一致的意思表示自由选择应适用的法律。该原则是法国法学家杜摩林(Dumoulin)首先提出的。从19世纪末以来,该原则在国际私法的许多领域被采纳,尤其成为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的重要原则之一。
但该原则在提单的法律适用上比较复杂,争议也较大。其中有学者认为,提单通常都是由承运人所准备的格式文件,法律适用条款早就印在提单的背面,并没有经过当事各方的协商,尤其在提单流转到第三人时,更不可能是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因此认为这种条款是应该被法院否定的。在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案例,如在台湾法院审理的一个案例中,承运人甲是委内瑞拉人,从印尼的某港口装运一批货物至台湾。提单上载明适用美国法。台湾进口商(托运人以外的第三方提单持有人)持提单向承运人索赔货损,法院认为不应适用美国法,因为该法律适用条款不是提单持有人参与共同选定的,因而不应约束提单持有人。法院最后选用了提单签发地印尼的法律。当然大多数国家在一般情况下是承认这种条款的效力的。笔者也认为应该承认这些条款的效力。单据的流转是海上运输的一个特点,因此承运人不可能和每个有关的当事人都坐下来协商法律适用条款,各国制定有关的法律和缔结国际公约,规定了承运人的义务和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限制承运人的缔约自由,从而保护货主的利益,因此没有必要再去否定提单上的法律选择条款。对交易而言,法律关系的稳定性比公平性更加重要,况且,大多数航运公司的提单条款都是固定的,经常打交道的客户对这些条款也是明知的,因此也可以事先作出对策。此外,大多数提单在提单正面右上方或右下方都印有“托运人、收货人以及提单持有人接受或同意提单所有内容”的声明接受条款以加强提单上法律选择条款的效力。总之,承认这些法律选择的条款对于当事各方而言,利是远大于弊的。
(一)法律选择的方式
1、单一法律选择
有的提单的背面条款规定提单适用一个法律(体系)。如某提单规定:“本提单应按照1924年《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定的国际公约》(简称海牙规则)的规定发生效力”这样的规定清晰明了,受理案件的法院根据法院地国的国际私法原则,在案件的法律适用上没有前两项原则可适用的情形下,一般就可以直接采纳了。又如:广州海事法院在审理“柯兹亚轮迟延交货纠纷”一案中认定:“五矿公司、班轮公司一致同意以1924年的海牙规则作为解决本案纠纷的法律。五矿公司与班轮公司双方选择法律适用的意思表示,不违反中国法律,应确认其效力。…”
但对法律适用条款指明受我国没有承认的国际公约约束时,(对中国法院而言,尤其指海牙规则)该法律适用条款的效力如何,学者们有不同的见解。一种观点认为应承认其效力并予以适用。理由是我国《海商法》只规定第四章适用于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没有规定其强制适用于出口和(或)进口提单。所以,即使约定的海牙规则中的每件或每单位100英磅的单位责任限制低于《海商法》规定的每件或每货运单位666.67计算单位的限制,也不能认为是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另一种观点认为应否认其效力,理由是我国没有参加该指定的国际公约,该国际公约在我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不应算是一种实体法。因此提单首要条款所指向的该国际公约的内容只能作为提单的条款并入到提单中,提单上的其它条款原则上不能与之相冲突。但是,该国际公约的法律效力却需依法院地国冲突规范指向的准据法的规定来确定。公约条款与准据法不相违背的,则有效;如有违背的,则违背的部分无效。该学者因此认为,合同当事人可以选择的法律似应指国内实体法,不应包括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笔者认为第二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有关提单的三个公约是统一的实体规范,当然包括在法律的范畴中,那种认为当事人可选择的法律不包括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的说法是没有依据的。《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中的一般法律适用条款中就明确规定,提单或提单所证明的合同规定适用本规则时,该规则便适用于此提单。如果公约不能适用于非缔约国,公约又何必作此规定呢?实际上,多边的国际公约被非缔约国的当事人选择适用更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航运界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也反映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精神,只有当事人才能根据自身利益,在不同的法律中选择出适用于提单的法律。只要是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法律规范,都可作为当事人法律选择的对象。如果因为国际公约在非缔约国没有强制性而不能被选择,那么任何他国的法律在内国都是没有强制性的,为什么可以被选择呢?基于同样的原因,将提单首要条款指向国际公约看作是提单的并入条款也是没有根据的,提单的法律选择条款指向某国际公约时,该国际公约对于提单的法律关系就具有了法律约束力,提单的条款与公约内容冲突的部分无效。而提单的并入条款则完全没有这种效力。
此外还要再区分一下两种强制性规则:一类是内国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们在本国法律体系内,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但是,如果它们并非合同准据法的一部分,则不具有这种效力。另一类则是冲突法意义上的强制性规则。它们不仅不能通过合同排除适用,同时也不能借助法律选择而排除此类强制性规则的适用。只要合同满足一定条件,该强制性规则就直接适用。显然本文中所论述的第一项原则论述的强制性规则就属于第二类。我国《海商法》的第四章的大部分条款确实是强制性条款,但该法并没有规定什么样的提单必须强制适用本法。只有我国《海商法》被确定为提单的准据法之后,这些强制性的法律条款才能起作用,因此,我国《海商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属于第一类。在我国《海商法》未被指定为提单的准据法时,《海商法》中的强制性规则对案件是没有法律约束力的。因此那种认为《海牙规则》减轻了承运人的责任,违反了我国法律的强制性,所以不能被适用的观点是混淆了这两种强制性规则的结果。而且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不光《海牙规则》不能在我国适用,任何他国的法律与我国的强制性规范冲突的,均不得在我国适用。事实上,我国法律中的强制性规范是普遍存在的,这样一来,几乎没有什么他国法和国际公约可以在我国适用了。这样的结论与国际私法的目的和精神相违背的。
当然为了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利益,我们也可以效仿美国等国家,在《海商法》中规定:“对外贸易中进出中国港口的海上货物运输必须适用本法”。这样,提单上规定适用《海牙规则》的条款自然无效了。但在法律修改之前,我们应该遵守现有的法律。
2、复合法律选择
复合法律选择是指当事人在提单中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这是在提单的背面条款常见的情况。这又分三种情形:
第一种情形称分割的法律选择。国际上关于合同的法律适用有两种理论,即“分割论”与“单一论”。总的来说,“单一论”主张对整个合同适用同一法律,“分割论”则主张合同的不同方面适用不同的法律。“单一论”与“分割论”都有其存在的客观依据。“分割论”反映了合同关系的各个方面和诸要素之间往往相对独立又特点各异的复杂情况,对合同的不同方面加以科学的划分并适用不同的法律,有利于合同纠纷的妥善解决。当然分割也必须有适当的尺度,即只应对于明显易于且可能区分的方面加以分割,对于一些内在联系紧密且不易或不宜分开的问题便不宜硬性分割。“单一论”则力求克服分割论可能带来的缺陷,使合同处于一种比较稳定的法律状态,它符合现代国际经济生活所要求的快速和简捷。但“单一论”往往忽视合同关系的复杂性,难以满足当事人的正当期望,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分割论”和“单一论”就应该取长补短,配合作用,才能最终达到合同法律适用的目的。这一作法是有利于维护国际合同关系的统一和稳定。
一般来说,只要允许当事人进行法律选择,那么他既可以作单一的法律选择,也可以作分割的法律选择──规定他们之间的国际合同的不同部分受他们选择的不同法律(体系)的支配。不少国际公约就有这样的规定。如1980年欧洲共同体在罗马签订的《关于合同义务法律适用公约》规定,合同可以分割选择所适用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适用于合同的全部或部分的法律。又如1985年在海牙签订的《国际货物买卖合同法律适用公约》第7条第1款也规定:“买卖合同受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支配,…这种选择可限于合同的一部分。”
中国远洋运输公司的提单背面条款第2条规定:“本提单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管辖。本提单项下或与本提单有关的所有争议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裁定;…”,第3条又规定“有关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应适用于海牙规则,即1924年8月25日在布鲁塞尔签订的关于统一提单若干规定的国际公约。”该两条规定应表明当事人同意在案件涉及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的方面适用《海牙规则》;案件的其它方面适用中国法律。
但是也有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这两种条款的性质是不同的,前者称法律选择条款(ChoiceofLawClause),又叫法律适用条款,是提单中指明该提单引起争议适用某国法律解决的条款。这一被选定的某国法律即为提单的准据法(applicablelaw);后者称首要条款(ParamountClause),是提单中指明该提单受某一国际公约或某个国家的某一特定法规制约的条款。他认为首要条款是作为当事人议定的合同条款被实施,而且该条款仅调整合同的某些事项或在特定情况下适用。首要条款是否有效力,应根据提单的法律选择条款中约定的准据法来决定。只要首要条款的内容不与该准据法的强制性规定相抵触,应该承认首要条款的效力。否则,首要条款无效,不予适用。
这种观点同样是值得商榷的。我们知道,关于提单的国际公约和国内法几乎都是强制性法律规范,三个公约和各国的国内法在承运人的责任、义务、权利及豁免方面差别较大,这样一来首要条款规定某些方面应适用的法律几乎肯定要和法律选择条款中规定应适用的法律相冲突,按照上面学者的观点,首要条款被适用的可能性是极小的。当事人又何必在提单背面费尽心机订立首要条款呢?笔者认为,既然要运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就应该尽可能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尊重当事人的意志。从中远提单中不难看出,当事人显然希望在案件涉及承运人的义务、责任、权利及豁免的方面适用《海牙规则》;而案件的其它方面适用中国法律。
此外,首要条款即是法律适用条款是海商法界的约定俗成,重新为它定义是没有必要的,而且这种区分是没有根据的。笔者认为这两个条款都是“法律适用条款”或“法律选择条款”,只是当事人在此作了分割的法律选择。
第二种情形称重叠的法律选择,这种情形是指当事人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但这些法律(体系)并非分别支配提单,而是共同在整体上支配提单。比如日本某航运公司的提单背面条款规定,本提单受《1957年日本国际海上货物运输法》和《海牙规则》的约束。又如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万宝集团广州菲达电器厂诉美国总统轮船公司无正本提单交货纠纷案中认定,本案所涉提单首要条款约定,因本提单而产生的争议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或1924年《海牙规则》,该约定没有违反中国法律,应确认其效力。上述两个提单上的规定就是典型的“重叠法律选择”。虽然“重叠法律选择”似乎可以用来满足各方当事人的愿望,但是,显而易见,在所选择的法律规定相左的情况下,就会使提单关系的稳定性受到损害。因此,有关当事人应当尽量避免作“重叠法律选择”。一般来说,如果所选择的法律规定是相互抵触的,由于提单是一方制作的格式文件,根据现代的合同法精神,应该适用于不利于提单制作人的法律规定。
第三种情形称随机的法律选择,是指当事人选择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体系),但这些体系并非分别支配提单的不同部分,而是分别在不同的条件下,各自从整体上支配提单。例如,中远提单第27条规定:“关于从美国运出的货物,尽管有本提单的任何其它条款,本提单应遵守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的规定。……”(这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地区条款)显然,中远提单背面条款的规定已经构成一种特殊的法律选择,称之为“随机的法律选择”。“随机的法律选择”是在充分地考虑将来某种事件的出现的基础上作出的,它可以照顾到当事人所从事的国际交易发展变化的不同情形,富有灵活性,因而也是有实践价值的。
(二)选择特定具体的法律还是选择某一法律体系
当事人在提单的法律选择时可以选择某个特定具体的法律,如,《美国1936年海上货物运输法》,1924年《海牙规则》;也可以选择某个法律体系,如中国法律、英国法律。选择后者,比较容易处理,因为一般一个法律体系都包括审理案件所涉及的各种法律问题。但当事人如果选择的是前者,这里又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选择特定具体的法律只能称作“法律并入”(incorporationoflaw),意为这种法律选择的功能是将所选择的法律并入到提单中,成为提单条款的一部分。因此被选择的法律对该提单而言已经不再是支配其的法律,支配提单的法律只能是当事人另外选择的,或按照其它的有关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所确定的其他法律。如果“并入的法律”与支配提单的法律相违背,自然是无效的。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有违当事人选择具体法律时的初衷,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相违背的。既然当事人选择了某具体的特定法律,那么,该特定法律就应当是支配提单的法律。当然,任何特定的法律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通常不可能支配提单的所有方面的法律问题,这是正常的。对于当事人所选择的特定法律客观上无法解决的法律问题,自然应当依据当事人另外选择的,或按照其它的有关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所确定的其他法律。这与我们上面讨论过的“分割论”的理论是一致的。
当然,当事人可以将某些法律规范并入到合同中,成为合同的条款,这在租船合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是由于调整租船合同的各国法律大多数是任意性规范,因此合同中的条款通常也就是约束合同当事人的最终条款,所以在此类合同中采取“法律的并入”是有意义的,即使如此,也需要当事人在合同中作出“法律并入”的明确意思表示。而对于提单,这种“法律并入”是没有太多意义的,因为调整提单的各国法律规范或国际公约多是强制性法律规范,而且彼此差异较大,被“并入的法律”通常无法得到适用。因此,当事人在提单条款中选择某一具体的法律,是不希望被作为“并入的法律”处理的,除非他们明确表示愿意这样。
除了在“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中会遇到这个问题。在适用前两项原则时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强制性规则”和国际公约都是具体的特定法律,它们都不可能解决提单所有方面的问题。因此同样在适用特定的法律无法解决的提单的其它方面,也应依据法院地国的其它的法律适用的原则所确定的法律解决。还有一个问题是,在第一项、第二项原则被适用的情况下,与其冲突的当事人法律选择条款是不被适用的,但它能否支配这两项原则所指向的具体的法律规范无法解决的问题,笔者认为是可以的,因为当事人选择的法律是想支配整个合同的,前两个规则的优先适用并不能完全否定当事人所选择的法律去支配提单剩下的其它方面的法律问题。
四、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原则
无论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还是“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法律适用规范,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这就是在解决法律适用问题过程中所具有的灵活性,亦即柔性。与此相反的是,在历史上以及在现实中,都存在着一些确定地规定着国际合同适用某法或不适用某法的规范,通常称作“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从这个意义而言,本章中的第一原则的法律适用规范也是“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之所以与前者区分开,是因为前者是单边冲突规范,是强行适用的和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而这里所指的“硬性法律适用规范”是双边冲突规范,是不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往往是在当事人未就法律适用达成一致时才被采纳。此外,并不是各国的提单国际私法规范都有“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如我国《海商法》第269条只规定了“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和“最密切联系原则”。但仍有不少国家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之后,“最密切联系原则”之前规定了“硬性法律适用规范”。因此,笔者将该原则作为提单法律适用原则的第四序列,和大多数国家的规定是一致的。“硬性法律适用规范”的连接点通常主要有:
(一)船旗国
在本世纪之前的早些时候,英国法院常常倾向于以船旗国法作为支配国际海上运输合同的准据法。1942年意大利的《海上运输法典》第10条也规定:在当事人未作其他的意思表示时,租船合同或运输合同受船舶国籍法律的支配。然而,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和司法实践却表明:以船旗国法作为提单的准据法,已经略显过时了。之所以如此,除了别的原因以外,一些国家奉行“方便旗”制度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在“方便旗”制度下,船旗已很难再表示船舶国籍的归属。这样,“船旗国法”就可能与船舶的真正国籍国法相背离;而且随着船旗的变换,有关提单的准据法也发生变换,这种情况显然是人们避犹不及的。
(二)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
按照波兰、捷克、前民主德国等国的法律,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国际运输合同应当受承运人的营业地(住所地)法的支配。以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法作为国际海上运输合同或提单的准据法的最大优点,是富有稳定性,因为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一般是比较固定的。它的另一个优点,是富有可预见性—只要托运人了解此种规则的存在,那么,他就知道了在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提单受什么法律支配。但按照此规则,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托运人便被置于承运人营业地(住所地)法的支配下,这看来是不公平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可以被人们指责为该规则的一个缺陷。
(三)合同订立地
按照某些国家的法律或司法实践,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时,他们之间的国际海上运输合同受合同订立地法的支配,例如,根据1968年《苏联海商法典》第14条第11款的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未达成协议,则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受合同订立地法律的支配。但是,如我们早已看到的,合同订立地的确定,有时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在国际海上运输交易中也是这样。比如,承运人可能在不同的国家有其当地人,而当地人可以承运人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这样,不同的当地人在不同国家订立的海上运输合同,就须受不同国家的法律支配,虽然合同的承运人并没有变化。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
(四)法院地
按照1970年《保加利亚海商法典》第12条第1款的规定,在当事人未作出法律选择的情况下,有关的国际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应受保加利亚法律的支配。这一规则似嫌武断,而且也是有违国际私法精神的,目前,很少有国家这样规定。
五、最密切联系原则
最密切联系原则在本章所讨论的法律适用原则的先后序列中的位次是靠后的,各国的法律通常将它排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及硬性法律适用规范之后,但在实践中这项原则被广泛地采纳,理论界的成果也较多。“最密切联系”原则学说是在批判传统冲突规范的机械性、僵硬性的基础上产生的,与传统的冲突规范相比,具有灵活性,从而有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然而,由于“最密切联系”这一概念本身的抽象与模糊,若不对该原则进行适当的限制,就无法减少或避免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这同样也是不利于案件公正合理地解决的。因此在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要尽可能做到既能防止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又能保证案件处理结果的公正、合理。
我国海事法院在审理涉外提单纠纷案件时,经常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但在运用此原则确定提单应适用的法律时,却有较大的随意性,有的案例中,仅写明:“原告与被告未在合同中约定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法律,应适用与合同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解决本案纠纷。由于本案货物运输的目的港是中国汕头港,故本案适用中国法律”,也有案例只是简单地写明:“综合考虑,中国与本案合同纠纷的联系最密切,因此,应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本案。”这种适用法律的方式是违背法律的严肃性和稳定性的,这也容易在个别法官中形成一种法律适用的僵硬的公式:只要当事人没有选择法律,一般就适用法院地法,只是罗列几个连接点,把“最密切联系”原则作为依据而已。显然这与创立“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初衷相违背的。
针对“最密切联系”原则灵活有余,确定性不足的特点,欧洲国家发展了一种“特征性义务”(“特征性履行”)的理论,即是指以履行合同特征义务当事人的营业地法或住所地法来支配该当事人所订立的合同。“特征性履行”的方法,一般总是排它性地或选择性地以单一具体的连接点为据来确定支配国际合同的法律的,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接点是抽象的,不具体的,因此两者的本质应该是不同的,但“最密切联系”原则可以把“特征性履行”作为推定其连接点的一种方法,即将履行合同的特征性义务当事人的营业地所在国或其惯常居所地国推定为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这样“特征性履行”方法就成为“最密切联系”原则的组成部分之一了。1980年《欧洲经济共同体关于合同债务法律适用的公约》就有这样的规定;我国198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涉外经济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第6款就用“特征性履行”的方法规定了13种合同的法律适用规范。虽然这种方法有可能保证法律适用结果的公正与合理,但当某一合同纠纷表明其与他国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时,仅依这一原则显然是不能达到目的。因此1987年《瑞士国际私法》以及上述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解答中都规定,如果情况表明合同与其它国家或地区的法律有更密切的联系,就可使该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地之法得到适用;对法律未以“特征性履行”方法规定的其它涉外合同关系,仍要以“最密切联系”原则作指导,以确定其准据法。
对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提单法律关系,不同国家的法律或国际公约在运用“特征性履行”的方法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结果都不同。如,1975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关于国际民事、家庭和劳动法律关系以及国际经济合同适用法律的条例》第12条规定,对于货物运输合同、承揽运送合同,其合同应当分别适用运输人、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地的法律。但也有的法律对运用“特征性履行”方法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法律适用进行的推定,规定了较严格的条件,如欧洲共同体于1980年6月19日在罗马签订的《关于合同义务的法律适用公约》第4条规定,货运合同在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也是装货地或卸货地所在国,或者也是托运人的主营业所所在国,应推定这个国家为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1986年德国民法实施法第28条第4款规定,货物运输合同得被认为与合同订立时承运人的主要营业地国家有最密切联系,如果该国同时也是货物装运地或卸货地或收货人主要营业地所在国。我国法律则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提单的法律适用未进行推定,因此法院对此类案件在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特征性履行”方法毕竟只是适用“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一种推定的方法,在具体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时,仍必须对案件事实所反映出来的合同要素进行全面细致的分析。客观地看,所谓“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指的是与合同本身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但合同本身是由各种合同要素构成的,所以上述“最密切联系”便只能通过合同要素与一定国家之间的联系表现出来。因此我们要用“合同要素分析法”来具体运用“最密切联系”原则。“合同要素分析法”通常包括两个部分,即“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
1、量的分析
一般来说,对合同要素进行量的分析可以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确定有关的具体合同的基本要素总量;第二步,分析这些合同要素在有关国家中的分布数量。以海上货运合同为例,其合同的基本要素可归纳如下:
(1)合同的谈判地;
(2)合同的订立地;
(3)提单的签发地;
(4)货物的装运地;
(5)货物的卸货地;
(6)合同标的物所在地;
(7)当事人的住所地(营业地、惯常居所地);
(8)当事人的国籍;
(9)合同的格式特点;
(10)合同中使用的术语;
(11)合同使用的文字;
(12)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
(13)合同中所约定的支付价金的货币;
(14)合同的经济与社会意义等。
确定合同基本要素的总量是对合同要素进行量的分析的基础,受案法院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运用“合同要素分析法”作进一步的分析。
接下来,就要分析合同要素在有关国家中的分布数量,任何一个国际合同,它的要素都不可能集中于一个国家,而只能分布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国家。假如有这样一个案件:日本货主与中远公司在广州经谈判协商,订立了一个货物运输合同,装货港在日本,目的港在中国,提单是中远公司的格式提单,是用英文制作的,提单上载有“受中国法院管辖”的条款,支付运费的货币是美元。货物到达中国港口后发生纠纷。在这个案件中,合同要素的分布的情况是这样的:与中国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的谈判地、合同的订立地、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国籍和营业地、货物的目的港、合同标的物所在地、中国公司的格式提单、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与日本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当事人之一的国籍、营业地、货物的装运港;与美国有关的合同要素是:支付合同价款的货币及使用的文字;与英国和其他英语国家有关的合同要素是:合同使用的文字。上述情况表明,合同要素的相对多数是集中在中国的,而合同要素的相对少数则分散在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来说,应当认为: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相对多数的合同要素常常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这些合同要素的集中通常就已经客观地表明了:合同本身与有关国家的联系是更多一些的。但是,这一结论并不具有绝对性,因为关于合同要素的质的分析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对这一结论作出修正。
2、质的分析
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而言,这些合同基本要素的地位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合同的要素地位较弱,如合同中使用的文字和支付价金的货币。有的合同的要素地位较强,比如合同中的法院选择条款。这是由于合同当事人选择了某一特定国家的法院,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他们对该国法律制度的信赖。而且,当事人选择了某一特定国家的法院,这通常就排除了其他国家的法院对该合同案件的管辖权,使被选择的国家的法院对该合同案件具有了管辖权。这种管辖权使该国法院与该合同案件之间产生了紧密的司法联系,这种司法联系是其他任何合同要素所不能造成的。
但大多数合同要素的地位是随着不同种类的国际合同或同一种类的国际合同发生不同的争议而变化的。比如,争议是关于合同是否成立,那么,“合同订立地”或“合同谈判地”这样的合同要素便应予以充分注意;倘若争议是关于合同履行的,那么,“合同履行地”这一合同要素便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等等。
通过对合同诸要素的量的分析和质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对于确定“与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这个连接点来说,各合同要素的意义是有所相异的。不仅集中于一个国家的相对多数的合同要素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那些地位较强的合同要素也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至于那些分散于不同国家的相对少数的合同要素,以及那些地位较弱的合同要素,他们一般是没有决定性意义的。
免责声明以上文章内容均来源于本站老师原创或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仅供学习和参考。本站不是任何杂志的官方网站,直投稿件和出版请联系出版社。
专业解答,全程指导
免费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