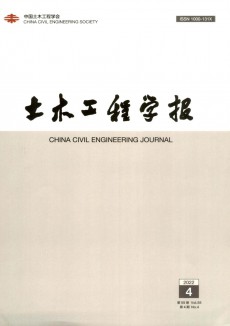土木工程认识论文大全11篇
时间:2023-03-30 11:28:34绪论: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抒发,也是对学术真理的探索,欢迎阅读由发表云整理的11篇土木工程认识论文范文,希望它们能为您的写作提供参考和启发。

篇(1)
物理学的发展使得自然科学各个学科和领域的以突飞猛进的熟读得到发展物理学在20世纪以来更是站在了科学的前沿,推动了新技术、新产业的进步,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可以说,物理学的发展是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教育的摇篮,首先,物理是理工科学生学好后续专业课程的基础,例如信息工程系中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要求学生有一定的电学知识,建筑工程系的土木工程要求学生有一定的力学知识基础。其次,物理的学习过程会使学生掌握和学习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能够进一步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开阔思路、激发他们探索和创新的精神,真正提高人才素质[1]。
近年来,大学物理的基础地位正面临危机,教学时数逐渐减少,受重视的程度也在不断降低。但物理学领域在高温超导、纳米技术等应用领域取得了很大成就,人才向应用领域转移。因此,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大学物理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注重思维方法和科学素质的培养,重视实践环节,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2]。
课程是高校实施教学过程的主体工程,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课程的有效性。课程是学生成长的养料,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性工程。课程的有效性程度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程度。有效教学是一种现代教学理念,以学生发展为主旨,强调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关注教学的有效性,提倡教学方式的多样化;同时,有效教学也是一种教学实践活动,必须以遵循教育教学规律为前提,以合乎教学目标为实质,以实现教与学的统一为关键。
大学物理课程的有效性包括教学的有效性和教育的有效性,而教育的有效性是以教学的有效性为前提。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学生进步和成绩是否达到了预期的目标,是否促进了学生的知识、技能、态度的全面发展。要求教师有能力判断学生是否达到这些要求,而现在学生学习兴趣不高、课时极度被压缩,教学大纲基本没有发生变化的情况下,需求一种有效的教学方式来适应现在的物理教学。对于应用型学院来说,高效低耗的课堂、有效的教学是十分必须的。高等院校也迫切需要改变这种教学低效的现状,而争取实施有效教学。提高课堂有效性的方法有多方面的,仅在一下几方面加以讨论:
一、在教学设计或实施的过程中注重能力或者素质的训练与培养
大学物理以知识为载体,探索物理方法、启迪物理思维、渗透物理思想、培养科学精神。物理学培养学生科学世界观:时空观、运动观、完整的物质世界图像;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清晰地物理思想、系统的物理思维方法;创新素质能力:独立思考、善于提问科学问题能力。创新思维能力:以基本物理思想为前提,利用猜想、类比、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分析物理结果,分析判断物理结果正确性的能力;将所学的物理知识应用于其他学科及实际问题的能力,独立地分析和解决物理问题的能力:概括物理现象、建立物理模型、抽象物理原理的能力[3]。
二、教师苦练教学基本功,深度挖掘教材
要突出教学重难点就要深度挖掘教材,深刻理解教材内容。不仅要发掘教材中的重点和难点,在授课时做到突出重点、突破难点。还要发现不同教材的证明、推导和计算方法的区别。物理教师对这些问题有了深刻的认识,在课堂上能够引导学生,训练积极、发散的思维。每一个教师,上课前准备愈充分,教的会愈好。充分的准备还可以应付学生即时的需要。
三、在保证完成基本教学要求同时,突出重点内容
参照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提出的《非物理类理工学科大学物理课程基本教学要求》[4]。每节物理课在标题上就要突出本节课的重点、难点。同时教师要进一步明确对于学生的知识、技能、态度目标的要求,学生素质提升的要求。针对重难点内容有选择性的进行分解,使得大部分同学能够听懂本次课,或者至少有一部分内容是懂了的。也可以利用网络资源查找课上要用到的 生动、有趣、与实际生活相关的图片引出本节课内容,所选图片要包含本节课所讲物理原理,能够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
四、大学物理教学中融合高等数学知识
大学物理与高等数学关系密切,从常量到变量、从标量到矢量,不少学生在第一次翻阅大学物理教材时,看到书中大量的高等数学符号,不由得对大学物理课程产生畏难心态[5]。大学物理最常见的思想是将载流导线、某一截面或位移分成无数多个无穷小的微元,从而等效达到已知的状态”,其处理思想就是高等数学中的微分思想。凡是应用微元思想后,其叠加过程皆离不开积分,如果说微分更大的作用在于提供一种思路,提供一种可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那么积分则是将思路转化为结论,将过程推演出结果的手段。
五、增强学生的课堂注意力
提高课程导入的艺术性。用物理学的最新进展与应用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运用幽默的语言提高学生注意力。有效的课堂,师生的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课堂上的交流反映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课外交流可以是生活中的实际交流,也可以是不受时空限制的网络交流。营造民主的教学作风,和谐的课堂人际关系是加强师生课外交流的有效途径[6]。
大学物理教学要在教育理念上富有时代特色,课程设置上要新颖、实用,紧密联系就业市场的需求与专业特点[7]。物理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科学技术的基础和带头学科,作为理工科专业的大学生,大学物理是其重要的公共基础课程,它所阐述的基本概念、基本思想、基本规律和基本方法是学生学习后续专业课的理论、逻辑基础;同时,它也是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创新能力的重要课程。为了有效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质量,在大学物理教学过程中,我们要主动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教学观;认识物理课程的阶段性教学规律和教学特点,促进学生物理认识能力的发展,不断优化教学,提高大学物理课程的教学效果[8]。
参考文献:
[1]边静.地方工科院校大学物理教学内容改革探索.山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2]朱小芹,唐煌.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大学物理课程体系研究.江苏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10,16(2),76-78.
[3]张晚云,陆彦文,曾交龙.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措施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学报.2010,33(4),119-120.
[4]教育部高等学校非物理类专业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分委员会.非物理 类理工科大学物理实验课程教学基本要求[M].北京:教育部物理基础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2010
[5]胡俊丽.刘兴来.扩招形势下提高大学物理课堂教学质量的举措.物理与工程.2012,22(4),53-54.
篇(2)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3)01-0023-07
收稿日期:2012-10-26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2012年度省级一般资助课题“知识类型及相关教学研究”( XJK012BGD049);2012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以TOC为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课程教学模式研究”(湘教通[2012]401号文486)。
作者简介:彭道林(1969 - ),男,湖北天门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讲师,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基础理论研究。
应用型人才和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中国高等教育目前流行的两个概念,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热门话题。然而,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是否具有足够的理论依据?是否具有概念本应具有的明晰性?新建应用型本科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多大意义?这些问题都是值得再思考的。
一、现有的关于应用型人才及应用型本科的论述
关于应用型人才,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具有相关的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面向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或专业人才,其知识和能力特征强调明显的应用性和实践性”,并且其知识应该由“基础知识、学科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三大要素组成,具有“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1]的特点。
关于应用型本科,也有比较权威的说法。中国的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被分为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第三种类型是多科性或单科性职业技术型学院(高职高专);而介于其中的则被称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并指出它有四个特点:第一,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第二,以培养本科生为主;第三,应用型本科应该以教学为主;第四,应用型大学应该以面向地方为主。
有关应用型人才培养和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研究也是围绕这两种基本的界定而展开的。那么,这两种界定是否能够作为研究的基础呢?
应用型人才的上述定义,不仅冗长,就说“基础实、能力强、素质高”这三个特点,即便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国内顶尖大学培养的学生,也很难是完全具有这些特点的。那么,这对于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有什么实际的指导意义呢?
更为基本的问题是,我们凭什么把人划分为“XX型”?雅斯贝尔斯有句名言,“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在本质上是不可计划的”[2](P36)。他还说,“每一种教育的作用也并非事先能预料的”[2](P65)。大学可以对学生提供侧重于应用知识的传授、应用能力的培养,但是,最终每一个个人到底是走向理论研究还是从事应用开发仍有不确定性,这取决于个人而非被他人“塑造成型”。即使有某种特定的目标,也不是为了框定或是像翻砂那样造型。教育是提供,而不是塑造;教育是培养,而不是框定;教育是期盼,而不是造型。真正的大学应该秉承着让学生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人的理念,把学生自己培养成为自己,更高大的自己,更有鲜明个性的自己。在类似哈佛、斯坦福、MIT这样的大学里,对于学生的培养完全不必有一个预设的模型。即便是职业技术学院也只是基础理论知识比重较小,技术、技能知识偏多,但这种人才培养也有其多样性特点。学生发展前景也是多种多样的,职业转化的发生也是极为正常的。这与定“型”也不是一回事。
有学者将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的原则概括为五个方面,即“全面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相结合、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相结合、人才培养与学科建设相结合”[3](其中,第五条原则和其他四条是不相协调的),而将应用型本科教育的特征归纳为“价值取向体现行业性、设置目标体现应用性、课程设置体现复合性、培养过程体现实践性、人才评价体现多元化”[4](P34-37)。事实上,这些概括的原则和归纳的特征很难让人看出“应用型人才”与“非应用型人才”及其培养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至于普通高等院校定位和分类的问题,是由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钦定,某些高等教育学者对这种做法持支持的观点,其依据是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高等教育结构,必须主动适应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人才结构。但这种划分和定位来自教育的外部,而非教育内部的逻辑。这里就牵涉到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问题。
教育本身就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基于人,又为着人自身。从逻辑上说,它具有独立性,它的基本使命首先不是适应的问题。
关于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是否“必须主动适应”,就值得商榷了。
大学产生之后才具有了现代意义的高等教育,至今它还不到一千年的历史。大学最初产生在11世纪末的欧洲,当时欧洲的经济是相对落后的,11世纪正值中国北宋的鼎盛时期,其生产力水平在全球是无可争议的第一位。然而,大学却在经济落后的欧洲出现了,可见大学的产生与经济并无直接的联系。在随后的几百年的时间里,随着人类知识的迅猛增加,大学由传统的经典四学院(即神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哲学院或文学院)发展出了许多的学科和专业(相应地产生了更多的学院)。然而,不论社会制度如何更替、经济如何发展、社会需要如何变化,大学在产生之初最根本的一些东西一直保留着,那就是“心智的培养;以事实和逻辑证据为基础的客观性;说理的法则而不是权力的法则;广阔的个人自由幅度”[5](P10)。难怪布鲁贝克说,“大学的存在时间超过了任何形式的政府,任何传统、法律的变革和科学思想,因为它们满足了人们的永恒需要。在人类种种的创造中,没有任何东西比大学更经受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5](P30)
大学是人类智慧的产物,它并不为适应而生;大学既因智慧而生,又为发展人类智慧而在。这是谈论大学的其他特性与职能的前提和基础。大学绝不是一个消极的适应者,真正的大学既向着遥远的未来,又守望着悠远的过去。它在人类文明史中生,又在人类文明史中长,并为人类文明史添上浓墨重彩。
美国大学的办学层次是由大学根据自己的师资力量、科研层次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地预先划定的,更不是外部机构拿来框定和管理大学的。芝加哥大学几乎是与北京大学同时成立的学校,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便成为了世界一流大学,这既不单纯是经济因素,也不是可以预设的。而我们的北大至今也仍只在亚洲一流大学的边沿徘徊,这也不纯粹是经济问题或人为分类和定位的结果。
关于大学与经济、政治之间的关系,在《高等教育学导论》一书中有专门的篇幅论述。它以诸多的论据、从多个方面进行了严谨的探求,指出“在大学与经济的关系问题上,将两者关系作形式化、简单化、线性化(即作直接的、直线式)的理解是最大的缺憾,以至于由此难以真正理解大学”[6](P52),同时也提出了“经济越来越依赖于大学”[6](P39)的观点。而相对地,那种口号式的“教育的发展必须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相适应”的观点则多少有点显得苍白无力。基于这种观点而得出的关于大学的分类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特点的结论也就值得怀疑了。
二、基础理论的意义与地位
以上的分析并不是对于应用研究的否定,相反,我们希望在更加清晰界定相关概念的前提下进行探讨。这种探讨也许更具理论和现实的意义。有学者提出,“应用型本科教育……是相对于理论型本科教育、实用技术型教育而言的”[4](P34),这种说法相对前面的观点似乎更具合理性。
对于应用的理解,有必要从知识的分类入手进一步讨论。知识的分类属于科学学的范畴。由于分类标准的不同,知识的类别也就被划分得不一样。一种比较普遍的划分标准是根据知识的对象确定的。从大的方面来说,知识的对象有三:一是自然,二是社会,三是人本身,相应地也就有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人文知识。
还有一种分类是根据知识的层次来划分的,相应地也就有基础理论性知识、应用性知识和开发性知识(或工艺性知识),这三类知识之间是有一定的逻辑关系的。基础理论性知识是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乃至具有某种形而上的特征;而开发性知识(或称工艺性知识)是偏向实用的,可以说是具有形而下的特点;应用性知识则介乎两者之间,它兼具形而上和形而下的特点,不妨以“形而中”来描述它。
无论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还是人文知识都可分为理论、应用和开发(或工艺)三个层次。基础理论的普遍指导意义,在科学技术发展中越来越充分地显现出来。
有学者总结了人类历史上的四次科技革命①(见下表),并注明了发明者的学历和职业。我们就此表稍作分析。
从个案上来说,不排除个别应用研究先于理论发现的(例如瓦特发明的改良蒸汽机就先于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的发现,后者的精确表述产生于1853年)。然而,在普遍意义上,科技革命是依赖于基础理论的。第一次科技革命引发的欧洲工业革命,其原动力乃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发电机、内燃机、汽油内燃机、柴油机以及汽车的发明,离不开能量守恒与转换定律的发现;原子弹的发明离不开核物理理论;载人航天技术则仍是牛顿力学与宇宙科学的应用成果;核磁共振技术缺少了核磁共振理论的发现便无从谈起;克隆技术则源自于DNA双螺旋体的发现……这些事实都能说明基础理论是应用研究的原动力。
对于发明者个人的学历、职业的分析也能说明问题。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技术发明人尚与大学没有直接关系;第二次的八位中有五位接受过大学教育;第三次技术革命的九位代表人物不仅全部接受过大学教育,并且其中的7位具有博士学位,4人是大学教授;第四次所涉及的三位则全部具有博士学位并且本身都是大学教授。这些事实说明,随着科学的发展,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与所接受的教育关联度越来越大,博士和教授本身就需具备很高的理论水平。
我们还可以从发明者的国籍来分析。第一次科技革命的三位发明者中有两位来自英国,这与牛顿的经典力学发现于英国不无关系;第二次科技革命八位发明者中的五位来自德国,而那个时候的德国恰好站在了世界科学(包括基础理论科学)的最顶峰;二战以后,美国取代了德国的地位而引领着世界科学的发展,因而第三、第四次科技革命共计十二位发明者,九位来自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另外再分析一个案例。众所周知,德国是拥有世界上最发达职业教育的国家之一,其应用科学大学也相当发达。因而,有人以为,职业教育是德国的秘密武器。其实,一个更为基本的事实却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即德国拥有极为雄厚的基础理论研究能力,拥有众多的基础理论研究成果,德国的许多学者都有极高的理论兴趣和哲学兴趣。这使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拥有了雄厚的基础。
康德是德国历史上极具影响力的一位人物。若要说德国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那就是它哲学的发达及其深远的影响。康德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他被认为是对现代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启蒙运动最后一位主要哲学家。海涅曾盛赞康德,“德国被康德引入了哲学的道路,因而哲学变成了一件民族的事业,一群出色的大思想家突然出现在德国的国土上”[7]。的确,康德之后,德国出现了如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叔本华、胡塞尔、雅斯贝斯、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等一大批哲学家,哲学的繁荣理所应当地引领了科学的发展。
德国柏林大学的成立是近代大学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创办者是洪堡。他本人曾说,“若真要说我拥有什么别人没有的,那就是在柏林成立了新的大学”。洪堡对于大学的论述于柏林大学有极为重要的影响。洪堡认为,大学兼有双重任务,其中之一就是对于科学的探求。洪堡所说的科学即所谓的纯科学,“纯科学是不追求任何自身之外的目标”[8](P37)。纯科学完全不考虑应用和其他功利目的,这是为科学而科学、为真理而真理的典型观念。
洪堡还认为,“寂寞和自由……为支配性原则”[8](P39),值得关注的是“寂寞”这一原则有三层含义:其一是大学应“独立于一切国家的组织形式”;其二是大学应独立于社会生活;其三是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应甘于寂寞,不为任何俗务所干扰,完全沉潜于科学。关于德国古典大学,陈洪捷作过非常严谨的研究,提炼出了德国古典大学的四个核心概念——修养、科学、自由、寂寞①。这对于中国大学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哲学的繁荣、柏林大学的成立,使得德国的科学事业在19世纪取得了空前的成就,遥遥领先于世界,德国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的顶峰。据统计,“在1820~1919年中,40%的医学发明是由德国人完成的;1820~1914年,生理学中65%的有创见的论文出自德国人,德国人在1820~1900年中在物理学(热、光、电子和磁)方面的发明超过英法两国的总和。”[8](P1)(英法为当时科学发达的少数几个国家中的两个)。被恩格斯称为19世纪最伟大的三项发现: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其中细胞学说由德国人施莱登和施旺提出,能量守恒及转化定律也是最先由德国人迈尔发现,后由英国人焦耳和威尔逊证实,并于1853年精确表述出来。20世纪最伟大的三个发现(相对论、量子论和DNA的双螺旋体结构),其中提出相对论的爱因斯坦和量子论的普朗克均为德国人。德国大学在19世纪末深深影响了美国的大学,从而造成对世界的影响。
德国发达的职业教育无疑受益于其高度发达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样,美国、加拿大、日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有发达的职业教育,但他们同时也具有雄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强大的基础理论知识是发达职业教育的必要条件,世界主要国家无一例外。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也相当发达,正好说明了同一个问题。
基础理论是应用研究、职业教育的坚实基础和走向繁荣的源泉,缺少了它,应用也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很可能只会停留在模仿的层面上。
三、中国基础理论的状况
中国的基础理论存在明显的缺陷,主要表现在:
1.中国自古以来就缺乏基础理论研究的传统。中国古代,无论是在天文、地理、数学还是技术、工艺等方面,都为世界科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贡献是明显侧重于技术的,基础理论式的贡献极其稀少。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的科技史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他指出:“在中国古代数学思想史中,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严格求证的思想”[9]。的确,中国古代的数学是偏于计算而缺少论证的。不仅如此,由于古代中国的相对封闭,中国未能受惠于类似《几何原本》这样严格求证的著作。《几何原本》正式翻译成中文已经是17世纪的时候了,而完整的译出则晚至1857年。爱因斯坦也说道,“西方科学的发展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10],其中的“形式逻辑体系”就主要体现在《几何原本》之中。
中国古代技术性的成果在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的手中高速地转化为生产力。受惠于此,中国曾经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是这个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即便是到了晚清时期(之前的1820年),中国的GDP仍然位居全球第一(超过当时的美国15倍以上)。可是,也正由于实用技术曾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成功,对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相对淡薄也产生了影响,实用的思想则逐渐根深蒂固,“学以致用”是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天经地义的观点。然而,在之前至随后的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欧美诸强以及日本等国经济迅速崛起,中国则由经济最发达国家沦为经济落后的国家之一,其间的原因是发人深省的。文艺复兴之后,欧洲的知识爆炸性地增长,而中国对此茫然不知。缺乏理论知识支撑的中国,经济虽仍在发展但明显缺乏后劲,其发展速度远低于欧美国家。之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从而步入了落后国家的行列。
直到19世纪末,中国才意识到科学的落后导致国家的落后。中国是世界上主要国家中大学出现得最晚的。中国的第一所大学于1895年由清政府创办。和欧洲古典大学不同,中国大学从一开始注重的就是实用学科。1895年清政府创办的北洋学堂(天津大学前身)设“土木工程、机械工程、采矿冶金、法科四科”[11](P1544),1896年创办的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设“商务专科、铁路工程班”,后“增设电机、航海专科”[11](P1322)。可以说,中国大学是根据实业发展的需要来创建的。1898年创建的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所设之专科虽有所不同,但其宗旨仍是“讲求时务”。“学术自由”并潜心于学术研究的局面,也只在执掌的北京大学、梅贻琦执掌的清华大学以及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短暂地出现过,其中北京大学是中国保持这种学术精神做得最好的大学。从整个过程来说,自中国第一所大学的出现至今,中国大学里重实用轻理论的局面几乎没有根本的改变。
2.哲学的落后与哲学兴趣的微弱。德国的崛起得益于其哲学的繁荣,而中国的哲学相对来说是比较落后的。早在春秋时期,中国就曾出现过“百家争鸣”,可惜这种局面未能维持下来。中国古代有非常丰富的哲学思想,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德克·博德曾用二十年的时间将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翻译成英文,他称赞“在25个漫长的世纪里,凡西方哲学家所曾涉及的主要问题,中国的思想家们无不思考过”[12]。可叹的是,中国古代的贤哲对于哲学的探求仅仅停留在思考的层面,而未加以系统的、科学的论证,因而也不利于传承、延续和发展。史宁中指出了中国古代哲学未能得到西方重视、也未得到国人发扬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人从古代起就比较务实,对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我们的先哲们过于言简意赅,常常简单到没有定义,没有推理,只有结论,使人难于理解”[13]。严格说来,中国古代有哲学思想却并无具有系统理论特征的哲学。
3.近代以来基础理论成果极度匮乏。鉴于以上两点,其结果亦必如此。对人类产生长远影响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成果,诸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亚里士多德以及黑格尔所研究的辩证法,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培根的实证逻辑,康德的古典哲学,黎曼、罗巴切夫斯基所发现的非欧几何,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以及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及转换定律,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朗克的量子论等等,没有一样是出自中国人,中国人对于这类成果的贡献令我们汗颜!
四、基本的结论
我们对于“应用型人才”、“应用型本科”这两个概念,基于史实、相关文献和一些案例进行了分析,应可得出如下几个基本的结论:
1.由于人的发展的难以预期,把人的培养归于某种类型,例如“应用型人才”的提法是缺少学术依据的,基于这种分类的实践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们可以在大学里对学生侧重于某种类型知识的传授,某种能力的培养,但是,教育的结果有很多是未知的。中南大学的理论数学教学与科研并非全国最强,却出了个本科生解决了“西塔潘猜想”,这又一次证明了雅斯贝尔斯的论述是成立的。
2.大学的办学层次应该更多地交给大学自己根据本身的师资力量、科研力量来决策,并且这样的层次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力量增强了,办学的层次自然可以提高。机械地把大学分为几种类型,并由此归纳出某种类型大学的特点,既没有充分的理论依据,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并且,掩盖了问题的根结所在,对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建设教育强国,甚至建立发达的应用科学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是无益的。有人说,如果全国的高校办学都是这样,都挤上同一条道路,都奔清华、北大的方向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全国大学“都奔清华、北大的方向去”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假设,对这一假设的正误再加以评判就更没有必要了。
有必要向全国的大学发一条指令“你们不要奔北大、清华的方向去”吗?全国的大学有可能都办成北大、清华那样吗?中国的北大、清华多了吗?如果有数十所、百余所大学能够办到北大、清华的层次,中国不就成了教育强国了吗?未必这也错了,还显然错了吗?更何况,北大、清华也并不见得就是中国大学的终极目标,北大、清华至今还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它们本身就还有一段艰难的路要走。新建的大学就不能成为一流大学吗?和北大几乎同时期建校的加州理工大学、芝加哥大学、斯坦福大学已经分别拥有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早已是世界一流大学,谁能预测中国的第一个诺贝尔奖一定会出现在北大、清华?谁又能保证中国第一个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的一定是北大、清华而不是别的大学?全球排名前一百位的大学,美国占了一半左右,美国嫌多了吗?美国大学有极高的办学自,联邦政府从不干预。美国大学也无所谓定位,而是自由地发展。越是这样,越能出现更多的世界一流大学。
3.尊重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基础理论研究的兴趣是中国建设教育强国的必经之路。唯有雄厚的基础理论作为支撑,才有可能出现高水平的应用科技、发达的职业教育。教育管理机构如果要发挥作用的话,在这个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而中国的高等教育学者则责无旁贷地需要为此努力。恩格斯的一句众所熟知的话十分经典地阐明了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他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14]
陈洪捷对于德国古典大学四个核心概念的提炼是值得中国大学借鉴的,相应的成果早在十年前就出现了,为何我们的大学没有给予注意呢?对于基础理论的重视是需要长远眼光和广阔胸怀的,马克思是一位典型的代表。恩格斯在赞扬马克思时说道,“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15]。如果我们拥有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的眼光,将是中国大学之大幸,中国教育之大幸,也是中国之大幸。
随着社会的发展,功利的东西、实用的东西不可避免地进入了大学,大学在保持其基本操守的同时也作出了妥协。然而,真正的大学仍然是排斥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的。美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弗莱克斯纳就此曾论述,“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去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16]博克校长在哈佛大学35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也是值得人们反复思考的。他说,“……如果说350年来哈佛有一个贯穿始终的特点的话,那就是我们总在心神不定地担忧,即使在从外界形势看来没有任何理由这样时也是如此。当我们为取得的成就而高兴时,会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阵痛……”,他进一步分析“为了寻找我们忧虑的根源,我们最好从观察学校的外部环境着手……各种集团……希望利用学校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你将会发现他们都在强调哈佛的成就——在社会上的影响,基金的数量,在高级职位的毕业生的数量......但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描绘的,只是一幅对哈佛和其他大学真正贡献歪曲的图画……”[17]。而一位国内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却说很高兴地听到一些“211”工程大学,甚至是“985”大学都说要根据市场需求来培养人才。与博克和弗莱克斯纳不同的是,这种说法就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这种功利主义对于中国大学的伤害是毋庸置疑的,相比马克思的眼光、弗莱克斯纳的论述以及博克代表哈佛对于功利主义表示出的忧虑,这样的观点不可谓不值得警觉。真正的学者,最高的境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学术而学术,而不是强调某种功利目标。真正的大学不是一个数字,也不是一个符号。
1852年恩格斯在评价奥地利的大学时说道,“大学都办成这个样子:只容许它们造就充其量在某种专门知识部门可能有比较高深造诣的专家,但无论如何不允许进行在别的大学里可望进行的那种全面的自由的教育”[18]。整整160年过去了,恩格斯当年的批评对于当今中国的大学仍然是一针见血的。
参考文献
[1] 王云儿.新建应用型本科院校以能力为导向的学生学业三维评价模式探析[J].教育研究,2011(6):102.
[2] [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M].邹进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3] 岳爱臣.论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原则[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8(5):101-103.
[4] 史秋衡,王爱萍.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基本特征[J].教育发展研究,2008(21).
[5] [美]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6] 张楚廷.高等教育学导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
[7] 苗力田,李毓章.西方哲学史新编[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0:509.
[8] 陈洪捷.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9] [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337-338.
[10]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574.
[11] 顾明远.教育大辞典[K].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12] 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英文版编者引言)[M].赵复三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1.
[13] 史宁中.关于教育的哲学[J].教育研究,1998(10):10-14.
[14]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5.
[15]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7.
[16] [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17] [美]博克.哈佛350周年(1636-1986)校庆的讲话[J].转引自眭依凡.学术之魂[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298-308.
[18]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07.
In Query of the Concept of Applied Talents Education